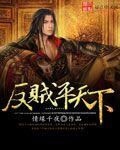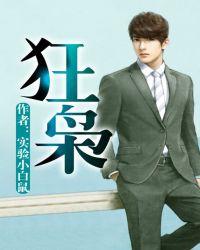秋天小说>恋爱疗愈手册 > 第123章 药(第1页)
第123章 药(第1页)
“吃饱了。”
“我一粒米饭都吃不下去了。”
“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弄演讲稿的事情了,之前你在家里也写了吧?”
在客厅里。
聚餐的饭菜也吃的差不多了,众人都表达了自己已经饱腹后,接。。。
雨丝斜织,街灯在水洼里碎成一片片光。林小满的脚步踩过那些晃动的光影,像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句子。陈默走得很慢,伞微微倾向她那边,右肩早已湿透。他没说话,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前方,仿佛在数着还有多少条街等着他们并肩走过。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几乎融进雨声,“我昨晚梦见了顾言老师。”
陈默侧头看她。
“他站在一间空教室里,黑板上写满了‘对不起’,可字迹都被雨水冲花了。我想走近他,但他一直背对着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没能救你,我是没能早一点听见你。’”她的手指收紧了些,捏住伞柄的弧度,“醒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不该只属于我一个人。”
陈默停下脚步,在路边的长椅坐下,收起伞放在一旁。雨水立刻打湿了他的发梢。林小满也坐下来,把两把伞并排靠在栏杆上。荧光线在灰暗中泛着微弱的光,像埋在泥土里的星屑。
“我们收到的那个男孩录音……”他低声说,“后来社工联系上了他父亲。那个男人开了二十年货车,从没请过一天假。听到录音那天,他把车停在服务区,坐在驾驶座上哭了两个小时。他说,他以为严格才是爱,结果孩子最想听的,只是‘你可以软弱’。”
林小满望着远处模糊的街景,一辆公交车缓缓驶过,溅起水花如时间的回响。“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人们总要把真心藏到最后?是不是因为害怕一旦说出口,对方会转身离开?”
“或者更怕的是??对方留下了,而自己却配不上那份回应。”陈默接过话,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画板边缘,“就像我以前画画,总想等准备好了再展出。可其实,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线条,才最接近真实。”
一阵风掠过,带来远处巷口飘来的桂花香。这味道让林小满忽然记起什么,从包里翻出那本《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书页随着翻动沙沙作响,干枯的洋桔梗轻轻掉落,她小心地拾起,夹回原处。
“你说,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进‘心语展’的‘遗物角落’呢?”她问,“不是作为展品,而是作为一个邀请??让别人写下他们想对某个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夹进书里。”
陈默眼睛亮了一下:“而且不设期限。谁都可以取出来读,也可以添上新的纸条。它会变成一本不断生长的对话录。”
“就像阿药第一次来我家那天。”她笑了,“瘦得皮包骨,蹲在门口不肯进来。我以为它需要食物,后来才发现,它只是需要有人愿意等它跨出那一步。”
手机震动。是社区中心值班员发来的消息:【今天有位母亲带着女儿来了三次。第一次不敢进,第二次站在门口看了十分钟留言墙,第三次终于写了张纸条投进信箱。她说,这是她女儿五年来说的第一句‘我想妈妈抱我’。】
林小满把屏幕递给陈默默看。他沉默片刻,掏出速写本快速勾勒了几笔??一个女人蹲在地上,双手张开,面前是个缩成小小一团的女孩,阳光穿过她们之间的缝隙,照亮尘埃飞舞的空气。
“画名叫《距离》。”他说。
雨渐渐小了,云层裂开一道口子,漏下一束淡淡的月光。他们重新撑伞前行,路过一家仍在营业的便利店。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少年正低头写作业,耳机挂着,手里握着半冷的饭团。店员阿姨悄悄往他桌上放了杯热牛奶。
“你看。”林小满轻声道,“温柔从来不在宏大叙事里。它藏在这些没人记录的瞬间。”
陈默点头:“所以我们才要替它们留下痕迹。”
第二天清晨,林小满接到市图书馆的通知:一位匿名投稿者连续七天在同一台终端上传音频,内容全是同一句话的不同版本??
【爸,今天降温了,记得加衣服。】
【爸,我学会煮面了,汤底放了葱花。】
【爸,昨天梦见你骑车载我去上学,你还骂我把书包挂后座上晃荡。】
……
最后一段录音背景有医院的心电监护仪滴答声:“爸,医生说你可能听不见我说话了。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不想见你,我只是……怕看到你躺在那里,再也喊不出我的名字。”
林小满立即联系家属信息库,查到患者正在城东医院ICU。她和陈默赶去时,老人已陷入深度昏迷,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床边坐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眼窝深陷,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
“这是我爸。”他声音沙哑,“三十年前我妈病逝后,他就把我送去寄宿学校,说男子汉不能靠眼泪活着。我们十年没好好说过话……直到上周他倒下。”
林小满递上录音笔:“他也许听不见,但身体记得语言的温度。您可以试着对他说话,就像他在听着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