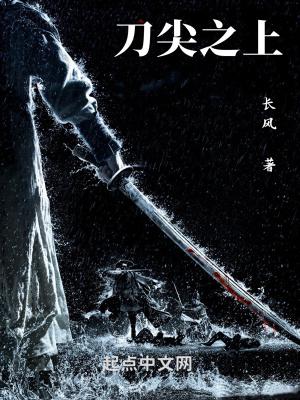秋天小说>我们全家都是疯批美人 > 8090(第4页)
8090(第4页)
有人给她披上一件外衣,“这就是殿下想到的‘办法’?”
谢崚抬头,发觉阿蒲就站在她的身前。
谢崚抬手拢了拢狐裘,道:“没错。”
她故意激怒慕容徽,让慕容徽对她发脾气,然后再顺势和他吵一架,再鬼使神差让留芳留下来。
以慕容徽对谢崚的宠爱,她这么做慕容徽除了吃下这个哑巴亏,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办法”也可以为谢崚省下一堆麻烦,将谢崚留下留芳的理由从“留芳有什么能入她的眼”变成了谢崚“留下留芳,不过是为了和慕容徽对着干”。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等了多久?”
谢崚蜷缩在毛绒绒大衣里,看着天空飘飞的白雪,屋内明亮烛火像是被封印在她红宝石耳坠中,微光随着她的侧耳轻轻晃动,白皙的下颌映着火光,隐隐发亮。
阿蒲忽然想起了,下午他用银针给谢崚穿耳的时候,她伸手搂着他的腰,死死不愿意放开,温暖的发香盈了满怀。
为了缓解紧张的氛围,他安慰她说道:“殿下别怕,奴婢数到三下,第三下就穿过去,一点儿都不疼的,殿下稍稍忍耐一下下,好不好?”
谢崚郑重点了点头,闭上眼睛,手上的力道却更大了,掐得他有些许腰疼。
“一,二……”
像是故意使着坏心思,数到第二下的时候,他没有数三,就将银针穿了过去,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洞穿她的另一只耳朵。
感觉到耳朵上的刺痛,几乎倒在他怀中的小姑娘闷哼一声,随即露出了一双明亮的眼眸,随即好奇地抬眼去看镜子。
阿蒲笑了一下,“方才过来的,等的时间也不久。”
绕到了她的面前,“能想出这样的法子,奴婢不得不夸一句,殿下聪慧。”
“既然你也觉得孤聪慧,那你可愿意做孤的谋士?”谢崚背着手,缓步走在雪地上。
做她的谋士,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还能收获聪慧的主公,这不好吗?
阿蒲笑着,“还不行哦。”
“什么时候才行?”
谢崚站在原地,疑惑地看着阿蒲,阿蒲朝前走了两步才意识到她的停留,微微一笑,温和谦卑的笑意,带着些许狂傲,“这可就要看我未来主公的修行如何了。”
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东宫。
进屋以后,阿蒲贴心地替谢崚脱下外衣,东宫里的侍从都会伺候谢崚,阿蒲也一样。
谢崚淋了雪,估计得沐浴更衣,阿蒲不能久留,正准备退下,谢崚却叫住了他。
“阿蒲,你等等,别走。”
阿蒲脚步一顿,谢崚站在屏风后喊他,“随孤过来。”
阿蒲勾起唇笑了笑,“三更半夜,殿下想要做什么?”
然而,当他绕过屏风的时候,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屏风的后面,端坐着一位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少年,一身红袍,满屋的烛火,被他的容色逼得黯淡下来。
方才见谢崚离席,苏蘅止就也起身告退,朝东宫的方向奔来,他的速度要比谢崚快一些,更早抵达主殿,泡好了茶水,在这里等候。
阿蒲在东宫将近两年,当然知道谢崚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他是不愿受燕皇之恩,撞剑而死的徐州太守苏令安之子,母亲为虞朝公主,和谢崚一起长大,生得灵秀美丽,年少多才,饱读诗书。
南朝女帝为他们降下婚约,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哪怕最后谢崚来到燕朝也没有分开过……可惜燕皇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女婿,将他调离谢崚身边。
阿蒲还是第一次见苏蘅止,脑海里无端生出了一个念头:好美的少年。
美得令人自惭形秽。
他低头,指尖缠绕着一缕鬓发,心想难怪谢崚会喜欢她,从邺城到龙城,无时无刻不在给他写信,总是惦记着他。
苏蘅止轻唤,声音清丽:“殿下。”
“这是阿蒲,我的书侍,之前我和你说过的。”谢崚道。
谢崚一直想要招纳却没有成功的谋士,虽为书侍,却不可以真的将他当成奴婢对待。
既然想要阿蒲为自己所用,谢崚干脆让他加入自己和苏蘅止的谈话,让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苏蘅止起身,给阿蒲搬来了蒲团,道:“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