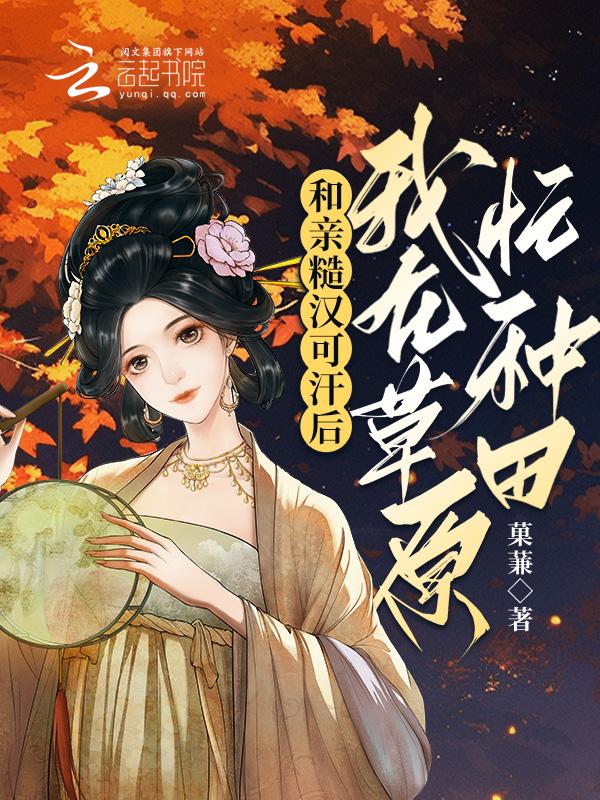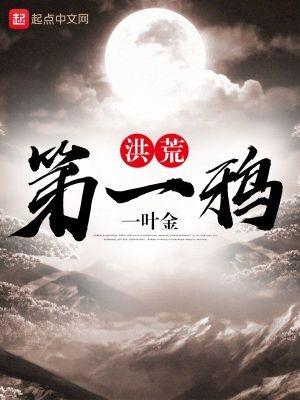秋天小说>从盛夏到深秋 > 岔路口的坐标与光影(第3页)
岔路口的坐标与光影(第3页)
页面迅速加载,教授严谨而平缓、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声音通过耳机清晰地传入耳中。
他下意识地坐直身体,脊柱绷紧,拿出崭新的笔记本和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翻开第一页,在页眉工整地写下课程名称和日期,然后开始一丝不苟地记录教授强调的要点,字迹清晰工整,条理分明。
习惯性地接受,高效地执行,不提出疑问,不制造任何可能偏离既定轨道的波澜——这是他在名为“家”的精密温室里,用了整整十八年时间,早已学会并融入血液的生存法则。
即使内心一片荒芜,程序也要完美运行。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南京。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完全是另一番光影交错、气息迥异的光景。
秋日的阳光不再酷烈,变得温柔而通透,透过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枝叶缝隙,洒下斑驳摇曳的光影,如同碎金,在地上跳跃。
古朴典雅的民国建筑群静静矗立,红砖墙上爬满了岁月痕迹的藤蔓,无声诉说着历史的厚重与悠远。
空气里混杂着古城特有的湿润气息和一阵阵若有若无、甜而不腻的桂花冷香,暗浮浮动,沁人心脾。
林叙背着一个洗得泛白、边缘起毛的帆布画板包,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看起来颇专业的金属测量工具箱,站在建筑学院那座爬满常春藤、有着拱形门廊的红砖老楼前排队报到。
他穿着一件同样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的浅蓝色格子衬衫,袖子一丝不苟地挽到手肘,露出清瘦而线条分明的小臂,肤色是经常在户外劳作才有的健康色泽。
肩上的帆布包鼓鼓囊囊,里面塞着他整个暑假在烈日下奔波于各个工地、一笔一笔攒下的学费和生活费、所有重要的证件材料、以及一本边缘已经磨毛、页角微微卷起的硬壳速写本——那是他最珍视的宝贝,记录着他无数个深夜的灵感与梦想,每一笔都凝结着他对未来的渴望。
在速写本的封底内侧,一个极其隐蔽的薄薄夹层里,安静地躺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边缘已经磨损的A4纸复印件。
上面,是他曾倾注所有心意写下的、永无可能寄出的“前程似锦”。它像一个沉默的印记,提醒着他,他曾那样纯粹而用力地、不求回报地喜欢过一个人。
那份喜欢,最终没有成为束缚彼此前行的枷锁,却也未曾在他心底真正熄灭。他不再需要、也不再期待对方的任何回应,却也无法说服自己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彻底从生命中抹去。
它已成为他的一部分,沉静地流淌在血液里,塑造着此刻的他。
报到手续在这座古色古香、充满人文气息的院办里高效而安静地完成。
没有冰冷的玻璃幕墙,只有打磨光滑的木制柜台和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文件档案。氛围松弛而专注。
梧桐叶缝隙漏下的阳光,在古朴的民国建筑红砖墙上跳跃,形成晃动的光斑。建筑学院老楼前,绿荫下的报到点充满了随性而至的艺术气息。
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迎新棚,几张看起来颇有年头的木质长桌随意摆放,上面堆满了建筑模型的边角料、各种型号的马克笔、颜料管和卷起来的、露出流畅线条的图纸,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松节水和铅笔屑的味道,一种独属于创造领域的混合气息。
“学弟!建筑系的?来来来!这边!”一个穿着宽松帆布工装裤、头发随意挽起,几缕碎发垂落额前,手上还沾着些许未干石膏粉的学姐(名牌:方晴,大四,建筑设计)热情地招呼林叙,笑容灿烂,眼神明亮犀利,“证件给我看看。林叙?好名字!很配你气质!干净又有点故事感。以后就叫你小林啦!”
她声音清脆响亮,带着一种不拘小节的、蓬勃的活力。
旁边一个戴着黑色贝雷帽、气质斯文安静的学长(名牌:赵哲,研一,建筑历史与理论)正低头帮另一个新生看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结构草图,闻言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温和地笑道:“欢迎加入。四牌楼校区是块宝地,这里的一砖一瓦,这些老建筑本身就是最好的、活的教材。”
他递过来一叠材料,“喏,这是你的宿舍钥匙、校园卡,还有系里前辈们自己整理编写的‘生存指南’,”那是一个手工细心装订的牛皮纸封面小册子,封面是手绘的校园地图,线条细腻生动,“里面避坑指南和周边宝藏小店都标好了,比官方的实用多了。”
林叙双手接过,指尖能感受到牛皮纸粗糙温暖的质感,低声道谢,声音因为长时间不说话而有些干涩:“谢谢学长学姐。”
方晴凑过来,大大咧咧地打量了一下林叙背着的厚重画板和那个专业的金属工具箱,眼睛一亮,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哟,装备挺专业啊!自己准备的?有基础?太好了!以后画图课、模型课你有福了!不过提前说好啊,咱们系馆通宵亮灯是常态,卷得很,做好准备啊小伙子!”她说着,用力拍了拍林叙的肩膀,力道不小,带着同行间的认可和“自求多福”的调侃。
赵哲则温和地笑了笑,补充道,语气更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别听她吓唬你。虽然确实辛苦,熬夜画图做模型是家常便饭,但当你最终做出自己满意的设计,看到图纸上的想法一点点变成现实,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值得所有的付出。”
他语气真诚,带着对专业的热爱,“对了,你的宿舍分配在文昌X舍XXX,是老楼,条件比较一般,没有独立卫浴,但很有历史味道,离系馆特别近,蹭工作室方便。”
林叙认真点头,将材料仔细收好,放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正准备离开去宿舍安置,听到旁边几个刚报到完、正聚在一起翻看那本手绘“生存指南”的新生在小声交流,声音隐约传来:“刚才那个赵哲学长气质真好,温文尔雅的,一看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
“方晴学姐好酷啊!又帅又美!手上那是做模型弄的石膏吧?感觉好拼,好厉害。”
“哎,你们看那个穿格子衬衫的新生,”有人用眼神示意林叙离开的清瘦背影,“背画板那个,感觉好安静,从头到尾话都没说两句。但是气质很特别,好帅啊。这身高得有一米八五以上吧?清冷挂的。”
“我好像排他后面登记的,叫林叙?听负责的老师小声说了一句,分数也不低呢,是综合分很高的成绩进来的。”
“看着有点……独来独往?不过搞建筑的,可能都带点艺术家气质?喜欢独处找灵感?但确实是有点帅哈。”
“他那个画板包洗得都发白了,看起来用了很久,不过那个金属工具箱看着倒是很专业,不像便宜货……家境可能比较普通?”
林叙没有回头,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将帆布包的带子往上提了提,背脊不易察觉地挺得更直了些,加快了脚步,迅速融入了梧桐树荫下稀疏的、抱着各种材料穿梭的人流,向着那座充满历史沉淀感的“文昌舍”走去。他的脚步踏在斑驳的光影上,沉稳而坚定。
在那间略显简陋却干净、充满了老木头味道的六人间宿舍里,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柜子,将那本厚重的、承载着梦想与秘密的速写本小心放入,也将那张承载着未诉心事的字条复印件,更深地、更安全地藏进了速写本的封底夹层深处。
那里,是他无人知晓的、沉默的青春墓志铭,也是他独自前行时,心底最柔软也最坚硬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