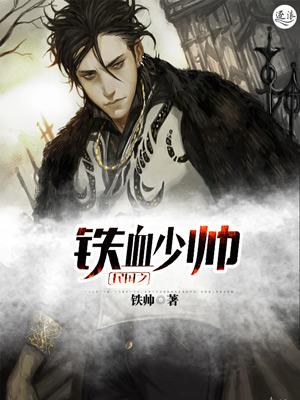秋天小说>Love you forever 之 鳶飛魚躍 > 第 49 章(第2页)
第 49 章(第2页)
说来也奇怪,写完之后,我就消气了。那张纸也没给他,他不配。
“嘉心”我妈敲了敲门,然后走进来问我要不要去大姨妈家,我说我不去。“你哥明儿就走了,你今儿还不去?……别再较劲了啊!”她说服了我,其实,是我说服了自己。
到了姨妈家,玄朗也在,我没看他,径直走进卧室。一会儿,妹妹洗完澡过来了,说要睡觉,但我不想因为她要睡觉就停止唱歌,所以她只得听着。我肆无忌惮地唱,兴致盎然。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的磁带听完了,屋里灯被打开了,是我妈进来叫我去洗澡。冲了个澡回到卧室坐在床边,看见我哥那屋的门开了,玄朗终于要回家了。他向家人一一道别,我别过头没看他。等他刚走出大门,大姨妈就和我妈快步走到我跟前批评道:“你怎么这样啊,哪有不看人家的?”“是啊,人家想跟你说话呢。”
“看他干嘛,等他想娶我了再看。”我没好气地说。
这时,大哥也从卧室出来了,我瞥了他一眼,没上去打招呼。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笑着说:“呦,怎么着啊,还跟我别扭那?”
“没有啊,跟玄朗,不是跟你。”
“大学准备考哪儿啊?”
“没想好呢。”
“考政法大学吧,当律师去,你这么能说,或者北京电影学院也成。”
“还有一年呢,不着急。”我可不想在北京待着,以前不想,现在更不想了。要不我也去戍边去得了,至少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马援不是说过吗—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哥,驻南使馆被炸了。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开战?”我岔开了话题,这是我哥最爱的话题—战争和政治
“操!我都想扛着枪当兵去了!他们只会谴责、抗议!有TMB什么意义?!”我哥瞬间爆燃,义愤填膺。
“不懂政治就不要乱讲。”一直半躺在沙发上的大姨夫发话了:“盼着中国打仗?拿什么打?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跟美西方一百多年的差距,你觉得中国有对抗美国的实力吗?我们不打不是怂,是要人民休养生息,真打起来,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你这血气方刚额年纪,还是多动点儿脑子。”大姨夫是我们的“政治导师”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又博古通今。
“四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还有一对新婚夫妇啊!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说着说着我哽咽住了,不止为牺牲的烈士们……
“小不忍则乱大谋。别说中国现在不能打,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能打。清朝的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让咱们被西方列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欧洲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咱们还在鼓吹康乾盛世呢。就是满清的夜郎自大让中国不论是在军工还是科技领域都开始呈现断层式下滑,你以为这是说追上就能追上的嘛?”
“文景之治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十年的事儿啊,后来刘彻不是把匈奴打服了嘛!这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血性啊!”我很不甘心。
“你说的对,但你知道文景之治之前,刘邦和吕雉隐忍了多少年?匈奴写信调戏吕雉,吕雉都只能好言相劝。后来刘彻穷兵黩武四十多年,把他爷爷和他爹卧薪尝胆几十年攒下的家业都败光了,你知道那时的老百姓过得多辛苦么?他又为什么要颁布《轮台诏》?”
“可是痛快啊!一想到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歼灭招降数十万匈奴人,多解气呀!”我兴奋起来。
“呵呵,傻孩子,霍去病是不世出的英雄,中国几千年不才出了一个霍去病吗!”
“还有陈汤呢?‘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地说出那句流传千古的金句,站起身挥舞着拳头。“现在说出来都还荡气回肠!!这才叫血性!虽然他后来贪污受贿吧,但瑕不掩瑜,哈哈哈……”我越说越亢奋。
“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要学历史,唐太宗内句话怎么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会儿只有匈奴,咱们都忍了半个世纪,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都蠢蠢欲动,抑制中国崛起的势头。我们现在开打,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不禁感叹道。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告诫我们,用兵一定要慎之又慎。”大姨夫补充道。
“啊?俾斯麦说‘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范围内!’咱们有核武啊!!操,看他们丫的服不服。”反正我哥还是不服。
“哎呀哥,杀鸡焉用牛刀?!”
“你看看这就是你崇尚的血性,可惜没有脑子。这会儿可不是冷兵器时代,好勇斗狠最吃亏。”大姨夫对我说道,同时瞟了我哥一眼。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就爱听我大姨夫讲历史,讲政治,尤其在讲国际局势时,总是高屋建瓴,字字珠玑。
我本来对历史挺感兴趣的,不幸的是,教我们历史的老师是外地人,口音特别重,而且说话时就像嘴里含着热茄子一样,吐字不清,让人昏昏欲睡。我就纳闷了,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行业的人不应该先学好普通话吗?!更不幸的是,我中学六年的历史课都是同一个老师!口齿不清也就算了,讲课还极为乏味,只知道照本宣科,没有任何延展。比如有一次她讲到史书有两种形式,一种叫“纪传体”,一种叫“编年体”。“编年体的史书是不能列为正史的,例如《资治通鉴》就不在二十四史中”。我问她为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她说:“显而易见,纪传体的,就是以人物为主题,用个人列传的形式阐述历史事件;编年体的,就是按照时间线,陈述历史事件。”我不知道是她以为我傻还是她自己够傻,这么明显的区别我用得着她解释么?我是想知道两者本质上的不同而不是形式上的,但她根本回答不上来。后来经我爸点拨才明白,因为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可以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阐述相同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所以对于同一件事或者同一个人就会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从而让我们看到更加客观地评说论断,而不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相形之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以服众。在我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发现,这本书可能都是司马光的队友编纂的,司马光本人只负责批阅而已。全书从战国时的三家分晋讲起,前几章经常能看到“臣司马光曰”五个字,越往后越少,感觉根本不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