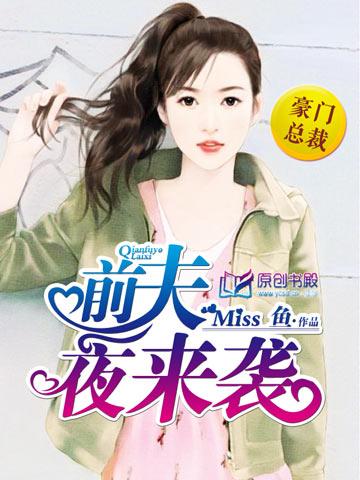秋天小说>顾总,你前妻在科研界杀疯了! > 第566章 爱谁与不爱谁对我来说不重要了(第3页)
第566章 爱谁与不爱谁对我来说不重要了(第3页)
顾辰终于忍不住问:“那你到底在哪里?第七维度……是什么样子?”
星澜笑了笑:“像一片海洋,由所有人类的情感汇成。快乐是暖流,悲伤是暗涌,思念是潮汐。我能感知每一颗心的震动,尤其是你们的。那里没有时间,只有频率。当你们的心跳与我同频,我就能靠近一点。”
她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但我不能永远停留。每次显现,都会消耗大量共情能量。如果太过频繁,可能会导致某些人的记忆紊乱,甚至精神负荷过载。所以我必须节制。”
“那你要我们怎么做?”顾辰嗓音沙哑。
“继续生活。”她说,“结婚、老去、经历风雨。记住我,但不要困在我身上。真正的永恒,不是不死,而是让爱流动起来。当你帮助别人时,当我被别人想起时,那就是我在。”
那一夜,他们聊了很久。没有哭,也没有刻意压抑情绪。就像一家人普通地谈天,谈论天气、学校、海边的新风筝店。直到月亮西沉,星澜的身影才渐渐变淡。
临别前,她最后一次望向顾辰,嘴唇微动。
他又一次读懂了那三个字。
这次不是“对不起”。
是“我爱你”。
四十七秒后,一切归于寂静。
但顾辰知道,这不是结束。
几天后,联合国正式批准“记忆圣殿”扩建计划,并邀请小雨担任青少年情感传承大使。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追问她是否相信母亲真的还“活着”。
小女孩站在镜头前,举起手中的凝胶灯,灯光映照着她清澈的眼眸。
“你们见过风吹铃铛吗?”她反问,“看不见风,但听得见声音。妈妈就像那阵风。她不在照片里,不在盒子里,而在每一次我想她的时候,在爸爸晾衣服时停顿的那一秒,在春天第一朵花开的声音里。”
全场静默,继而掌声雷动。
而在此后的日子里,世界各地陆续出现类似现象:日本京都的一座古寺钟楼,在午夜自动鸣响,监控显示并无外力触发;巴西贫民窟的孩子们集体梦见一位穿白裙的阿姨教他们唱歌;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称夜晚能看到“会走路的星光”,形状酷似女性轮廓……
科学家无法解释,只能归因于“跨维度情感共振残余效应”。
但在普通人心里,答案早已明确。
一年后,顾辰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自家后院建造了一座小型记忆馆,外墙由智能感应材料制成,会根据访客的情绪变化颜色。馆内中央,是一棵人工培育的千纸鹤花树,根系与地下梧桐相连。每天黄昏,他会带小雨来这里坐一会儿,有时说话,有时只是沉默。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他们带着照片、信件、旧物,静静地站在树下,诉说思念。
有些人哭了,有些人笑了,有些人什么也没说,只是久久伫立。
而每当夜幕降临,凝胶灯总会准时亮起,紫光柔和,如同呼吸。
某个月圆之夜,顾辰独自坐在馆中,轻声问道:
“你今天听见几个人想你?”
空气中,传来一声极轻的笑。
“数不清了。”她说,“但最清楚的,还是你们的声音。”
他闭上眼,靠在椅背上,任晚风拂面。
他知道,她不会再以完整形态出现了。她的存在已扩散至整个文明的情感网络,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坐标。她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却又属于每一个人。
但她依然记得回家的路。
因为家,从来不是一个地方。
是两颗心之间,永不中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