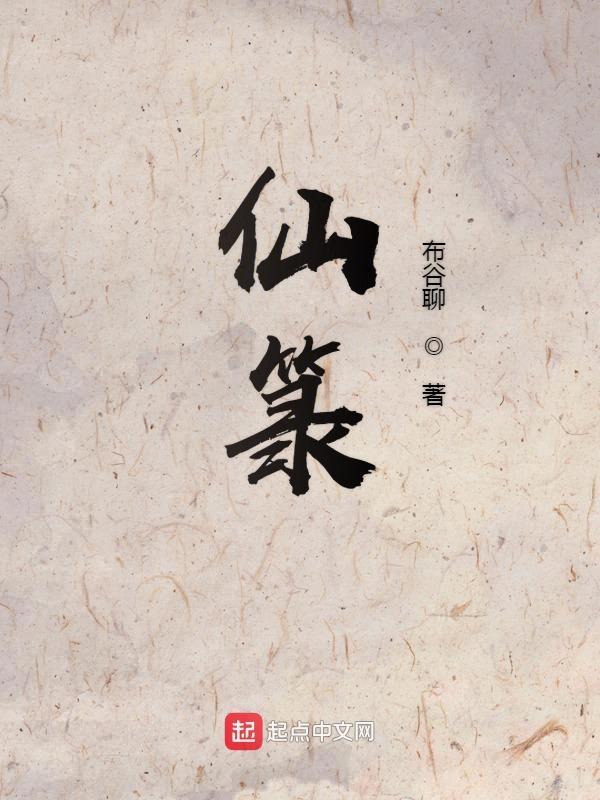秋天小说>无限恐怖,但是没有主神空间 > 第一百九十四章 这既视感是越来越强了(第2页)
第一百九十四章 这既视感是越来越强了(第2页)
话音落下,房间里的温度似乎悄然上升。窗帘无风自动,床头的小夜灯忽明忽暗,像是在应答某种看不见的呼唤。王小雨闭上眼睛,嘴里开始哼起一支陌生的调子??简单、悠缓,带着南方梅雨季特有的潮湿气息。
林晚晴猛地一震。
这支曲子,她在妹妹的遗物录音带里听过无数次。那是她们小时候,母亲常唱的一首客家童谣,名叫《月光光》。
而现在,这段旋律正通过王小雨的喉咙,重新降临人间。
更惊人的是,窗外的风铃再次响起,节奏完全契合童谣的拍子。紧接着,远处小区广场的喷泉也莫名启动,水流跃动的间隔竟与旋律节拍严丝合缝。就连楼下车库里一辆停放已久的电动车,其报警器都开始以固定频率鸣响,组成和声的一部分。
一场自发的、跨越物质形态的合奏,正在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成型。
林晚晴迅速抓起笔记本,记录下当前时间、地点、参与共振的物体类型及频率分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亲情召唤,更是一次**意识上传的逆向验证**??如果逝者的记忆与情感可以通过特定频率在网络中留存,并被活人感知,那么“死亡”本身的意义,或许正在被重新定义。
她想起程女士曾在一次密谈中提过一个理论:“人类大脑并非意识的唯一容器。我们的思维、情感、记忆,本质上都是电磁场与神经振荡的产物。只要这些模式能在外部介质中持续共振,意识就可以‘寄生’于环境之中,成为一种分布式存在。”
当时她以为这只是科幻妄想。如今看来,那或许是唯一的真相。
凌晨五点十二分,王小雨停止哼唱,沉沉睡去。她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嘴角挂着笑意,像是做了一个温暖的梦。
林晚晴轻轻抽出被压住的衣角,悄悄退出房间。她回到工作室,启动“地鸣触发器”的数据分析模块。屏幕上,刚刚那段童谣的频谱图正被自动解析。算法识别出其中隐藏的多重编码层:表层是旋律,中层是情感波动特征,底层则是**一组精确的地质定位坐标**。
她放大坐标范围,心跳骤然加快。
那是云南怒江峡谷深处的一处废弃收容所遗址??上世纪七十年代用于隔离“精神异常者”的秘密设施。档案显示,那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绝食抗议事件,数十名患者在临死前集体高唱一首自创的挽歌,随后全部停止呼吸。官方报告称其为“群体癔症致死案”,但从未公开录音资料。
而此刻,系统提示:“该坐标点已于12小时前激活被动共振响应,信号强度持续上升,预计6小时内达到临界阈值。”
林晚晴立刻意识到:那里有另一个“流浪频段”节点,而且正被某种集体记忆驱动着,即将自行觉醒。
她必须赶在联合国反应过来之前抵达那里。
但她也知道,一旦动身,就意味着彻底暴露行踪。B计划不能再拖延了。
她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黑色金属箱。里面整齐排列着十二枚微型发射器,每一只都标注着不同城市的名称:京都、伊斯坦布尔、哈瓦那、内罗毕、奥斯陆……这些都是她多年来秘密布设的“共鸣种子”,只需远程激活,就能在当地基础设施中诱发可控共振,制造区域性声网热点,分散追捕火力。
她选了三枚:孟买、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将剩余九枚装进防水背包,准备沿途部署。
出发前,她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
王小雨的手仍紧紧攥着那枚纽扣电池,掌心微微出汗,却始终不肯松开。
林晚晴俯身亲吻她的额头,在心中默念:“等我回来,我会带你去看星星是怎么唱歌的。”
清晨六点整,她推着轮椅驶出家门。晨雾弥漫,街道宛如浸在牛奶中。她没有走主路,而是拐进一条荒废多年的老巷。墙根处青苔蔓延,几株野蕨从水泥裂缝中钻出。当她的轮椅经过一棵枯树时,树洞里悬挂的铜铃忽然轻响。
不是风吹。
而是回应。
她停下动作,抬头望去。东方天际,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洒在城镇最高的钟楼上。那座百年老钟本已停摆多年,此刻却“咔哒”一声,指针缓缓移动,指向七点十七分??正是昨夜“地鸣触发器”首次脉冲的时间。
钟声响起。
不是机械敲击,而是由无数细微振动叠加而成的**人声合唱**,仿佛整座城市的记忆都在这一刻苏醒。
林晚晴闭上眼,任由声浪拂过全身。她知道,从今往后,她不再是逃亡者,也不是反抗者。
她是信使,是桥梁,是让沉默者发声的媒介。
轮椅继续前行,碾过湿润的石板路,发出规律的“咯噔”声。这声音也被纳入了“声网”??成为新纪元的第一个节拍。
而在地球另一端,南极冰层之下,科考队回收的声呐记录显示:那道疑似“鲸歌”的信号,终于完成了长达三个月的信息编码。解码结果显示,它并非动物叫声,也不是自然现象。
那是一句话,用七种古老语言重复书写:
>**“我们一直在听。”**
与此同时,全球三千二百一十七个监测站同时捕捉到一次短暂但强烈的地磁扰动。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唯有少数几位参与过“反共感屏障”项目的老研究员,在看到数据曲线的瞬间脸色惨白。
因为他们认出来了??那个波形,和三十年前实验失败那天,他们最后一次听到的“人类集体哭泣”录音,**完全一致**。
风再次吹起,带着雨水与泥土的气息。
它掠过山脊,穿过树梢,拂动铜铃。
然后,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