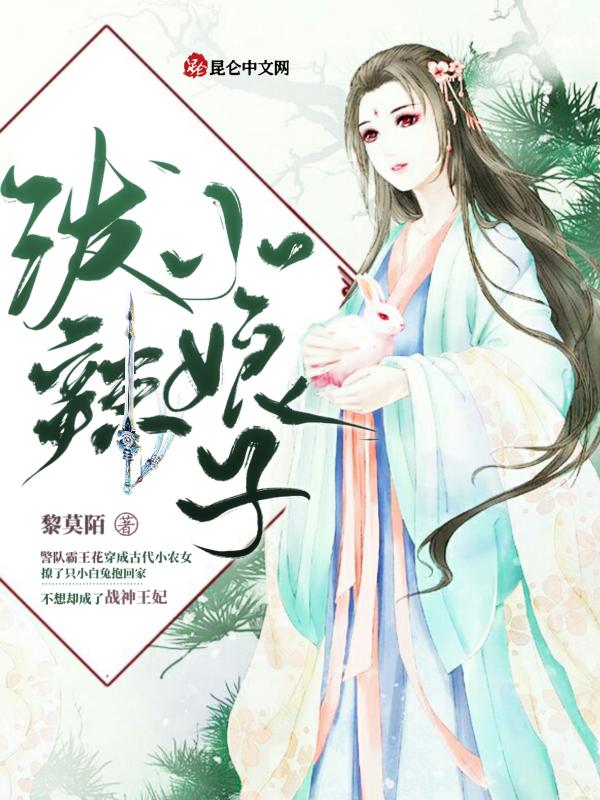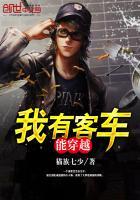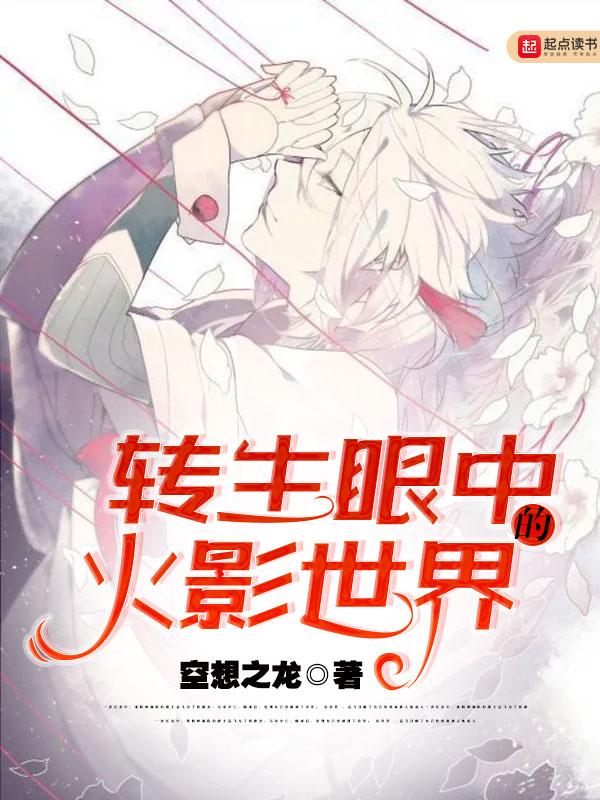秋天小说>豪商·女强 > 6570(第5页)
6570(第5页)
“哎,”明月摆摆手,“我就是做丝绸买卖的,也常往京城、杭州去,终究比旁人容易到手些。若非谈银子,我也不敢再住在这里,立刻叫人搬出去便罢了。”
说着,作势要走。
“哎呀你看看!”林太太一把拉住她,无奈笑道,“罢了罢了,算我多嘴。”
话虽如此,面上笑容却更盛了。
明月此举,便是发迹后也不忘本,依旧与这边长久往来的意思。
既是这样,谈银子算账确实不好。
那就收下!
大不了好生招待,来日遇到好食材,多多送些与她就是了。
“这就对了!”明月笑了一回,又压低声音,神秘兮兮道,“只对外别说是我弄来的,别家都没有呢。”
这番话便是彻底将王家与其他顾客家划分开来,算是自己人了。
众人果然高兴,纷纷点头,“我们晓得轻重,必不叫你难做,对外只说托人从州城买的就是了。”
反正全县上下皆知王大官人喜好穿衣打扮,又有钱,专程派人去外地买布也不算什么。
次日林太太私下里找到明月说话,拉着她的手道:“说实话,你来住,我是真高兴。”
明月反手握住她的,“我也高兴。”
王家上下是当初她来固县立足时,第一家率先表达出友善的大客,对明月而言,意义非凡。
林太太叹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闹腾,现在……”
她有一儿一女,女儿最贴心,可如今女儿也嫁出去了,身边骤然冷清下来,很不适应。
平时老太太忙着礼佛、看话本,王大官人又要照看外面的生意,林太太也忙,身边虽有儿媳帮衬,到底隔着一层,又是长辈和晚辈,就不那么随性。
明月这个忘年交一来,林太太攒了一年的话就都有地方去了。
明月耐心听她说着家长里短,时不时问一嘴,引出更多,又赞她在穿戴方面大有长进。
林太太乐得合不拢嘴,“都是你的功劳。”
“也是你衬得起,”明月笑道,“这回进京,我又看见两种时新发髻,有一种倒很适合你。”
林太太喜不自胜,“全赖你费心。”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话一点不错。
以往她不会打扮,十分懒怠迎来送往,总觉得会有人在背后笑话。又因不怎么出门,便更懒怠打扮,就更不愿意出门……
可自从明月帮她挑选妆容、搭配衣裳之后,周围的人都夸赞她装饰得体、舒展大方,林太太便渐渐自信起来,也不弓腰缩背了,许多以前撑不起的衣裳也很合适了。
如今她偶尔得了新衣裳,还很愿意主动出门走一走,引来更多赞美,然后就更愿意收拾自己,觉得生活多了许多乐趣。
明月看着眼前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的林太太,再回想当时黯淡无光、压抑躲闪的“小老太太”,真是天差地别,替她高兴之余,也有些得意:我也算做了件大好事吧!
又听林太太划算才得的那匹霞染,“那颜色极好,正是过节穿的,先叫针线上的人给老太太做一件,正月十五穿……”
等老太太穿过,晚辈就能接上了。
两人说了大半日,茶水都喝干两壶,林太太这才意犹未尽道:“差点忘了正事。来年七月是老太太的整寿,我和当家的都想大办,寿礼么,左不过是那些东西……我想着她老人家向佛,什么金玉佛像、名家挂画是不缺的,再送未免落了俗套,不如请你找个可靠的绣娘,绣一幅观音像,要近人高的,挂在佛堂里以示虔诚。”
明月细细问过要求和忌讳,心里就有了主意,胸有成竹道:“这个不难,包在我身上!”
王家做吃食买卖发家,年夜饭尤其隆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所不包。
桌子正中一道炸得金灿灿的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又有八荤八素并若干汤水、点心。
明月是贵客,王大官人便命人将鱼腹上的嫩肉夹与她吃了,又上自家酒窖酿造的果酒。
明月素日滴酒不沾,今儿却也放开了,几杯据说“不醉人”的果酒下肚,周围的动静便渐渐远去,然后睁眼就是天亮了。
苏小郎手舞足蹈地描述着昨日她醉酒的情形,“眨眼您就滑到桌子底下去了,大家都唬了一跳!”
明月:“……行了,闭嘴吧。”
这种细节就非说不可吗?!
正月初二,周家老爷子亲自来王家递话,说想送一个孙女跟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