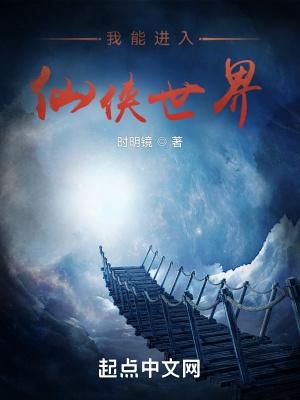秋天小说>豪商·女强 > 8090(第7页)
8090(第7页)
这件事前前后后牵扯太多时间和精力,明月已经没什么耐性继续同江平天天耗了。
没关系,凤翔府距离杭州也不过两个月的路,正月底派人去的,最迟五月底六月初就能回来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爹娘在手,看江平还怎么嘴硬。
不过借此机会,多结识个场面人也不错。
明月叫人备了一份节礼,不过是些糕饼点心之类,额外添了一匹湖水蓝的提花薄缎,一匹松石绿的轻罗,都是老少咸宜、男女皆可的颜色,正是夏日穿的,一并送给康捕头。
康捕头十分推辞,“不过捎句话,这……使不得。”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姑娘太难缠,万一日后提出什么他办不到的要求该如何是好?
然后明月转头就叫人送到他浑家手上了。
杭州再繁华,也同下头的小兵小卒没什么关系,康捕头只是个捕头,连个吏都没混上,家里父母、发妻俱在,又要拉扯三个儿女,并不轻快,故而虽身处丝绸泛滥之地,却鲜少买得起提花缎、轻烟罗。
人生在世,哪有不爱鲜衣美服的呢?
等康捕头回家,他浑家早便欢欢喜喜把料子铰开了,木已成舟。
康捕头不过多说几句,浑家便挥舞着剪刀叫屈,“是给我自己受用的不成?你睁着那双瞎眼看看,是我的尺寸不成?你娘活了一把年纪,穿过几回好衣裳?亲生儿子不上心,儿媳妇伺候还不行?”
康捕头有些心虚,躲闪着迎面飞来的唾沫星子,“两匹料子少说也得十多两,叫人……”
加上各样贴补,他一个月也才四两银子罢了。
“天底下只你一个青天,”他浑家阴阳怪气道,“人家进了衙门,爹娘老婆都跟着吃香喝辣,乡亲父老都跟着受用,偏你这不行,那不中……谁还会因为两匹布就砍了你的头?我且问你,这几日可有人叫你出去过节吃酒?”
康捕头一怔,下意识摇头,“问这些作甚?我可不出去乱花银子,更不曾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去!”
你自己不想捞钱,旁人想!你一味如此便是阻了旁人财路,长久下来,自然渐行渐远,有好事也没人想起你来。他浑家便冷笑着戳戳他的胸口,“糊涂东西,我倒是盼你出去日日应酬,好歹有个指望!”
说着,不再理会,继续埋头裁衣裳去了。
送来的有点晚了,不过料子很好,都带t着花纹,不必额外刺绣、排布,又是单衣,只需拼起来就是了,熬一熬,两日就能得,正好过节穿。
外头应酬有什么好?平平无奇一壶酒、几盘菜就要二两银子,够一家人吃多久了?想交际,自家买点菜蔬回来做不好么?又省钱又清净……
康捕头满头雾水,见浑家不理自己,摇摇头,转身出去换衣裳。可迈出去几步,脑海中突然亮了一下:是啊,为何无人相邀……
“依旧来我家过节!”
端午将至,就连水司衙门各处也轮流放假,林劲松照例邀请卞慈去他家。
“热燥燥的,怎好屡屡打扰……”卞慈推辞道。
哪怕再亲近,终究不是一家人,自己去了,嫂夫人和侄子侄女不免拘束。
“哎,你嫂子都说你是我的福星,巴不得你多去几次,”林劲松抓着他的手说,故意板起脸来,假模假式的威胁,“出门前我可是跟你嫂子立好军令状了,你可别叫我做难!”
这倒不全是奉承话。
官场之中处处虚情假意,林劲松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七年,日常与他称兄道弟的人不在少数,可都没用!唯有一个卞慈才来了没几年,就带着林劲松得了嘉奖、赏赐,再攒两次,说不定官儿都能升上一级半品的。
相比男人们更顾惜外面虚无的名声和所谓体面,谢夫人显然更看重实际:林劲松的官职越高,权力越大,她出门才更能挺直腰杆,以后孩子们的路才越好走。
退一万步说,就算林劲松本人有生之年升不上去,能交往一个前途无量的好朋友,对自家也是有利无害。
长女再过两年也该预备相看起来,而如今林劲松的品级很有些不上不下,高官厚禄之家攀附不上,下嫁白身又不甘心……女人嫁人便如第二次投胎,事关生死,故而谢夫人是真心的邀请卞慈去做客。
“林劲松林大人的邻居……”卞慈脑海中突然响起这句话。
鬼使神差的,他没有继续推辞。
“就这么定了!”林劲松大喜,抓住他的一边肩膀用力晃了晃,撂下这话翻身上马。
林劲松来去匆匆,此事也没瞒着,卞慈给大家排了班,便有新来的在私底下疑惑,“怎不见头儿家去过节?”
另一人不以为意,“朝廷要异地为官,大约是头儿不舍的家居往返奔波,还在家里呢。”
“头儿早几年就来了,哪有这么年轻的夫妻常年分居两地的!况且即便家眷不在,逢年过节也该叫人捎带点东西来,再不济也该有书信,可咱们来了这么久,立春、上元节、清明节、寒食……你可曾见过头儿接到什么?”一开始那人反驳说。
众人一听,哎,还真是。
以前没注意,如今回想起来,好像卞慈确实不曾提及家眷。
不,不仅是家眷,他身上似乎完全没有与“家”相关的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