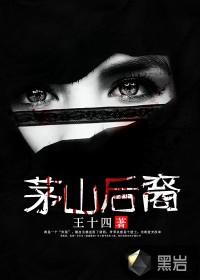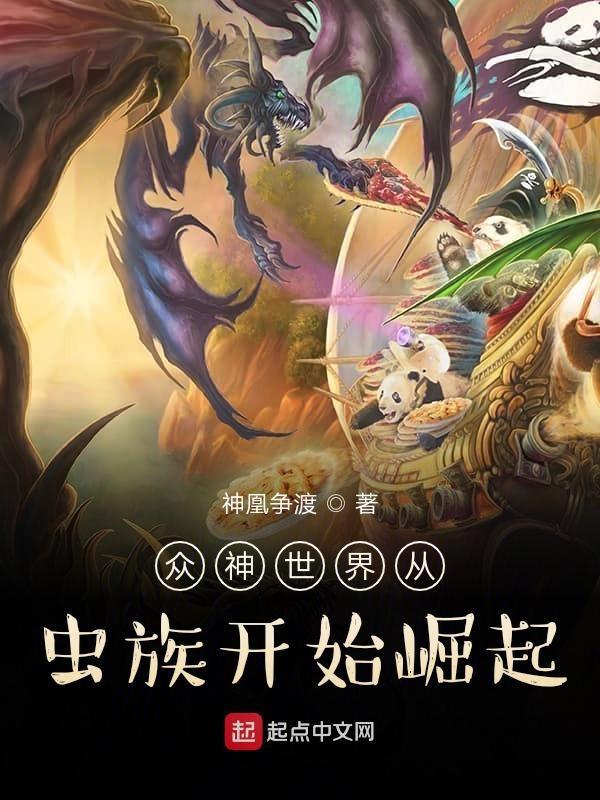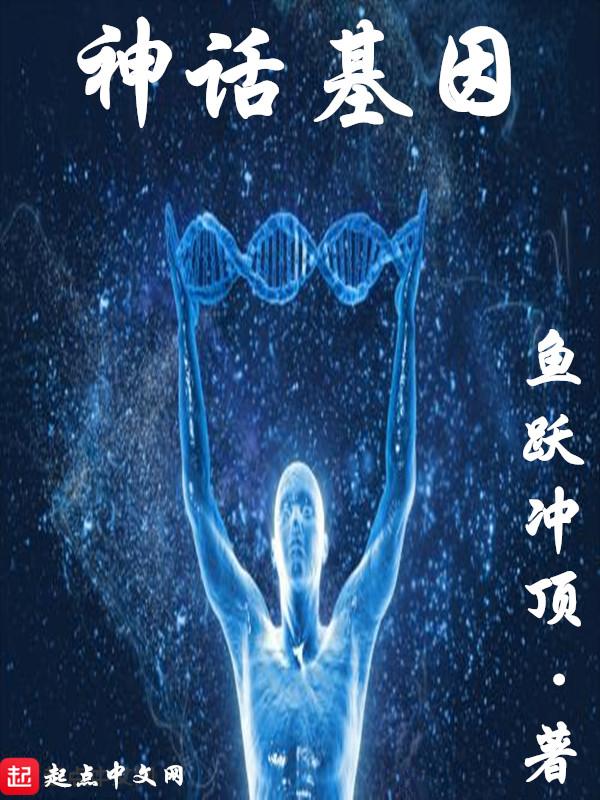秋天小说>大清王朝的兴衰 > 第2章 第二章 孤城遗民(第1页)
第2章 第二章 孤城遗民(第1页)
永平城陷第三日,雪停了。
天光惨白,照在断壁残垣之上,如同覆了一层死灰。城中火势渐熄,余烟袅袅,空气中弥漫着焦木、血腥与尸臭混合的气息。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穿甲胄的明军,也有百姓,甚至还有几具后金兵的尸首,被冻得僵硬,像一堆堆被遗弃的破布。
后金兵在城中肆意劫掠,马蹄踏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回响。他们破门而入,抢夺粮食、财物,强掳妇女。哭喊声、咒骂声、犬吠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着几声惨叫,旋即又被寒风吞没。八旗将士以户为单位,圈占民宅,将原主人驱赶至街头,任其冻饿而死。城中秩序荡然无存,昔日的永平府,己成一座人间地狱。
城西,一座破败的民宅中,李氏一家蜷缩在地窖里。
地窖低矮潮湿,仅靠一盏油灯照亮。李老汉六十有余,须发皆白,搂着年幼的孙子小满,轻声哄着。儿媳柳氏坐在角落,怀抱婴儿,眼神空洞。她的丈夫李大柱,原是城中一名铁匠,三日前在城破时为保护妻儿,持铁锤与后金兵搏斗,被乱刀砍死,尸首至今未寻。
“娘,孩儿饿……”小满抽泣着,小手抓着柳氏的衣角。
柳氏低头,从怀中掏出一块硬如石头的杂粮饼,掰下一小块,塞进孩子嘴里。她自己则咽了口唾沫,强忍饥饿。
“再忍忍……等风头过了,娘想办法。”她声音沙哑,却仍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李老汉轻叹一声:“这兵祸何时是个头?老汉活了六十岁,见过万历年的太平,也见过天启年的乱局,可从没见过这般凶残的鞑子!张将军守城时,百姓尚有活路,如今……唉!”
他想起张凤奇登城誓死那一幕,老泪纵横:“那样的好官,竟也……天理何在!”
正说着,忽闻地窖口传来响动。三人顿时屏息,柳氏急忙捂住婴儿的嘴,生怕啼哭引来灾祸。
“别怕,是我。”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地窖口掀开,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是邻居陈三,原是城中一名书吏,平日里读过几本书,会写会算,城破后便躲了起来。
“陈三哥!”柳氏松了口气,“你可吓死我们了。”
陈三钻进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脸色凝重:“外面乱得很,鞑子在抓青壮,说是充作苦力,挖城、运粮。被抓去的,十个有九个回不来。我亲眼见李铁匠家的二小子,才十五岁,被拖走时还在哭爹喊娘……”
李老汉浑身一颤:“我大柱的仇……还没报,如今又要抓小的?”
陈三摇头:“如今报不了仇。我来是告诉你们,后日正午,鞑子要在城隍庙前设‘归顺宴’,强逼城中士绅百姓前去饮宴,说是‘共庆太平’。若不去,满门抄斩。我听说,张将军的尸首,就被他们挂在城隍庙的旗杆上,任乌鸦啄食,以此威吓众人。”
“什么?!”柳氏惊叫一声,随即意识到失态,急忙掩口。
李老汉老泪纵横:“张将军……忠臣啊!他们竟如此辱尸!天理不容!”
陈三压低声音:“我打听过了,阿敏要在宴上逼士绅们写‘降表’,还要让几个读书人当众跪拜,以示臣服。若有人不从,当场斩首。我本不愿去,可若不去,全家性命难保……我来是想问问你们,要不要……逃?”
“逃?”李老汉苦笑,“往哪儿逃?城门有重兵把守,出城者格杀勿论。再说,这冰天雪地,妇孺如何走?”
陈三沉吟片刻:“我知道一条路——城北有座废窑,窑后有条暗渠,通向城外护城河。我小时候常在那里捉鱼,渠口虽窄,但人可匍匐而过。只是……极险,稍有不慎,便会冻死在渠中,或被巡城兵发现。”
柳氏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希望:“若能逃出去……小满或许还有活路。”
“可大柱的仇呢?”李老汉喃喃道,“我李家三代忠良,祖上还出过举人,如今却要像老鼠一样钻洞逃命?我不甘心!”
陈三低声道:“老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将军己死,我们这些百姓,能活一个是一个。若都死了,谁来记住这段血仇?谁来为张将军收尸?谁来告诉后人,永平是怎么陷落的?”
李老汉沉默良久,终于老泪纵横:“你说得对……我老了,死不足惜,可小满……他还小啊……”
柳氏紧紧抱住孩子,低声啜泣。
陈三道:“那便定了。后日正午,他们开宴时,城中必乱,守门兵也会松懈。我带你们走暗渠。但此事绝不能告诉第三人,否则走漏风声,全族皆亡。”
三人默默点头,地窖中一片死寂,唯有油灯噼啪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