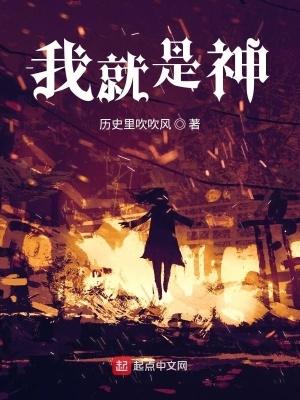秋天小说>大清王朝的兴衰 > 第2章 盛京风雪(第1页)
第2章 盛京风雪(第1页)
崇祯六年,十一月初三。
盛京(沈阳)的天,灰得像一块浸了水的粗麻布,压得人喘不过气。风从长白山方向刮来,卷着细碎的雪粒,抽打在城头的旌旗上,发出猎猎的声响。整座城池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静默中透着肃杀之气。
城外十里,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大臣,立于风雪之中,等候多时。
他身披玄色貂裘,头戴暖帽,面容刚毅,双目如电,虽己年过不惑,却仍英气逼人。身后是代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范文程等一众文武重臣,人人屏息,不敢言语。风雪中,唯有马蹄踏雪的轻响与旗帜的猎猎声。
“大汗,”范文程低声提醒,“风雪愈烈,尚可喜部尚在海上,或有延误,不如先回城中等候。”
皇太极摆手,目光依旧望向东南方向:“不。尚可喜率五岛军民,携船炮器械来归,此乃天助我大金。我若不亲迎,何以彰其诚?何以服众心?”
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铁:“昔年孔有德、耿仲明来降,我迎之三十里,封王赐旗,今尚可喜之才,不下于彼,且兵精械利,部众尤多。我若待之稍薄,恐寒天下归附者之心。”
范文程默然。他深知皇太极心思缜密,极善用人。自努尔哈赤开国以来,后金虽强于骑兵,然火器、水师、筑城、治理汉民,皆非所长。故皇太极继位后,极力招揽汉人降将,授以重权,编入汉军旗,以补其短。孔有德、耿仲明之降,己使大金火器大进,今尚可喜若来,东江水师之精锐,辽南地形之熟稔,皆可为我所用。
正思忖间,东南方向忽有烟尘扬起。
“来了!”多尔衮低呼。
皇太极眯眼望去,只见雪幕之中,一队人马缓缓行来。为首一人,身披铁甲,外罩黑氅,骑一匹乌骓马,身形挺拔,目光如炬。身后是数千将士,衣甲虽旧,却队列整齐,人人背负刀枪,肩扛火药箱、炮架、旗帜,更有妇孺老幼随行,牵马驮物,步履艰难,却无一人喧哗。
正是尚可喜。
皇太极脸上终于露出笑意,翻身上马,亲自迎上前去。
“来者可是尚可喜将军?”皇太极高声问道,声音洪亮,穿透风雪。
尚可喜下马,单膝跪地,双手捧上降书:“罪臣尚可喜,率五岛军民五千,战船二十七艘,火炮西十八门,器械若干,归顺大汗,愿效死力!”
皇太极急忙下马,亲手扶起:“将军何罪之有?将军能识天命,弃暗投明,实为智者!快快请起!”
他执尚可喜之手,大声道:“将军来归,乃天助我大金!我己为将军部众设营安顿,赐名‘天助兵’,以彰天命所归!”
“天助兵”三字一出,尚可喜身后将士无不动容。许多人眼中含泪,低声啜泣。他们漂泊海上,历经生死,只为一条生路,如今终得归宿,岂能不感?
皇太极又命人取来貂裘、暖酒,亲自为尚可喜披上,赐酒压惊。随即下令,全军入城,设宴款待。
盛京城内,早己备下馆驿。尚可喜部众被安置于城南新营,粮草、棉衣、医药一应俱全。皇太极更命户部拨银五千两,作为安家之资。此等厚待,令尚可喜部将士感激涕零,纷纷言道:“大汗待我等如子,我等当以死报之!”
当晚,大政殿设宴,皇太极亲自主持。
殿内火盆熊熊,暖意融融。尚可喜与诸贝勒大臣分席而坐,虽为降将,却位列上座,与多尔衮、代善同席。酒过三巡,皇太极举杯道:“今日得尚将军来归,实乃我大金之幸!将军忠勇可嘉,智谋过人,我欲授将军总兵官之职,统领旧部,编为汉军旗一旗,将军意下如何?”
尚可喜离席跪拜:“大汗厚恩,可喜粉身难报!然可喜有一请,望大汗允准。”
“将军请讲。”
“可喜旧部,皆辽东子弟,父母妻子多陷敌手,或为奴仆,或己殉难。今若编入汉军旗,愿仍以‘天助兵’为号,以存毛帅旧部之志,亦不忘来归之初心。且愿为大汗前驱,收复辽南,救我同胞于水火!”
皇太极闻言大喜,抚掌道:“好!好一个‘天助兵’!好一个收复辽南!将军有此志,我何愁辽东不定?”
他当即下令,正式设立“天助兵”,授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汉军镶蓝旗旗主之位,赏银万两,良田千亩,宅邸一座。并允诺,来年春暖,即命尚可喜率部南征,收复皮岛、旅顺等辽南要地。
宴至深夜,尚可喜被送至府邸。那是一座三进大院,朱门高墙,雕梁画栋,远胜皮岛陋室。可他却无心欣赏,独坐灯下,取出父亲尚学礼的遗甲,轻轻抚摸。
许尔显入内,低声道:“将军,大汗厚待,实出意料。然……我等毕竟是降将,位高权重,恐遭满洲诸贝勒忌恨。”
尚可喜点头:“我岂不知?皇太极虽明,然满洲旧贵,视我等汉人为奴仆,若无实绩,终难立足。”
“那……下一步如何?”
尚可喜目光渐冷:“大汗欲用我,必先试我。来年南征,便是我立功之机。我当亲率‘天助兵’,为大汗攻城拔寨,以血洗通敌之名,以功立不世之业!”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风雪未停。
他知道,自己己无退路。皮岛己成故土,大明视其为叛臣,而满洲诸贵,亦未必真心接纳。唯有以战功立身,以忠诚服众,方能在盛京站稳脚跟。
次日,尚可喜入宫谢恩。
皇太极待之甚厚,赐坐赐茶,问及辽南地形、皮岛防务、水师战法,尚可喜一一详答,条理清晰,见解独到。皇太极频频点头,对范文程道:“尚可喜之才,不下洪承畴,若善用之,辽南可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