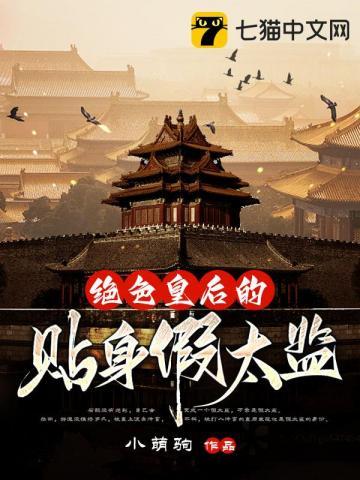秋天小说>龙傲天的金手指是我前任 > 90100(第7页)
90100(第7页)
花白头发,斑驳双眼,细密皱纹。
那是一张属于寿元无多、大限将至之人的脸。
“仙君随时可以带走你的那尊神塑,遗失神塑的后果,牧山一力承担。”
“牧山已奉上全部的诚意,赌上一切未来,”这张苍老的脸上嘴巴一张一合,“只愿仙君成全。”
这分明是一张与公孙罗完全不同的脸,可这两张脸却在她的记忆里重合,五官、年龄、形貌都不同,但他们的神情如出一辙。
是孤注一掷的表情。
记忆里,她目光灼灼。
“这是一场交易。”她一开口,就像一簇火在冰面燃烧,“我会守诺。”
如果公孙罗在山谷中听见的是这样一句回答,他绝不会惶恐不安地患得患失,直到即将分别时熬不住追问确认。
公孙罗在云淡风轻、无悲无喜的曲仙君身上无法找寻到的安心,曲砚浓有。
她欲望无穷、未斩悲欢,浑身上下都带着抹不去的、魔门留下的痕迹,但她有那样强大的、无可抵挡的魔力,叫人无法不信。
那张苍老的脸被她的承诺抚慰,绷得很紧的皱纹也稍稍张开,露出混杂着欣慰与苦涩的复杂神情。
这复杂的心潮终归会褪去,被一片苍白、茫然又空洞的东西所占据。
“还有一个问题,我本不该问……”老修士沉沉叹息,和她一起凝望那尊高大沉凝的青石神塑,用沙哑的嗓音缓缓说,“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仙君,我那个时乖命蹇的徒弟,他在仙君的心里,究竟算什么人?”
第93章孤鸾照镜(十一)
记忆里,她微怔。
说不上是什么心潮起伏,还不曾来得及涌到眉眼,她目光落在老修士的身上。
倘若情潮似水流,她的心绪就如沉静深海,就算海面下再多起伏,也没有一点轻易漫上眉眼。
牧山宗的老宗主、卫朝荣的师父,与她并肩站在那尊神塑前,语速很平缓,带着老人不自觉的腔调,习惯性地咬准每一个字。
“徊光他……一直很孤独。”年迈的牧山宗主絮絮地说,“几代人的期望都压在他的肩上,他性情太好,知道自己的使命,一声不吭地背负,从来没有过抱怨,钝学累功,没有偷过懒。同门都还在交游、玩乐,他已默默修习了一夜的刀法。有些拎不清的小子,还在背后拈酸吃醋,眼红徊光的天赋,也眼红我们对他的看重。”
“也算是牧山祖师显灵,既让徊光天赋出众,也让他重情重义。”老宗主说着,沉默片刻,“带他回蓬山那会儿,我也还愚钝,做事急功近利,看事不分明。其实徊光身上最大的优点,不是他的天赋,而是重情义、轻名利,倘若把谁当作自己的责任,他便能为谁赴汤蹈火。”
说到这里,老宗主终于回过头,将目光从神塑上挪到她的脸上。
那些有关碧峡魔女和一个被称作“血屠刀”的魔修的故事像风里的柳绵,看着满天满眼,风一吹全都散了,只剩下偶尔捕风捉影、荒诞不经的轶闻,没有人再想起。
除了始终留心的人。
“徊光去了魔域后,我一直暗暗地留意他的消息,听说他在魔域适应得很好,站稳了脚跟,魔修都叫他‘血屠刀’,害怕他的手段。我很为他担心,怕他迷失自我,但也为他欣慰。”老宗主望着她,“再后来,我听说了他和碧峡魔女的传闻。”
听说自己一手培养的弟子在魔域混得风生水起之外,还和魔域来历最不凡、身世最离奇、天资最出众的女修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老宗主那时的心情不可谓不复杂,既怕弟子染上魔修习性逢场作戏,又怕他身在局中动了真情。
“徊光最后能回来,我心里松一口气。我们都以为他会如释重负,可他却比从前更沉默,有时他就站在同门中,却像是隔了一方天地。”老宗主沉沉叹息,“时日久了,我才慢慢明白,他人在这里,可心却遗落在别的地方了。”
最初,老宗主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他明白了,可也已经晚了。
“我对仙君闻名已久,从前总是缘悭一面,如今有幸站在这里同仙君共听一段晚钟,这一问实在太晚,但又好在不太晚,赶在老头子寿元耗尽之前问出来。”老宗主定定望着面前神容灼目的女修,“徊光坠入情网是他自己的事,我只想知道,对你来说,他算什么人?”
是惯弄风月的逢场作戏,还是有点真情?
这问题没意义,这答案也不重要,但不平、不解堆积到大限之至,作为这不称职的师与父,他要为自己的弟子问个明白。
数百年后的曲砚浓在这问题里屏住呼吸。
记忆里,片刻的沉默后,数百年前的曲砚浓回答那个与卫朝荣关系匪浅的老修士,“不是什么人。”
在老宗主脸上涌现强烈不平与不值之前,她又开口,重若千钧。
“在我心里,他是卫朝荣。”数百年前的曲砚浓说,“卫朝荣就是卫朝荣。”
情人、爱侣、同类、知己……
那都太复杂,又太简单。
人怎么能用言语概括另一个人,怎么够?
“他是卫朝荣,就只是卫朝荣。”
什么人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