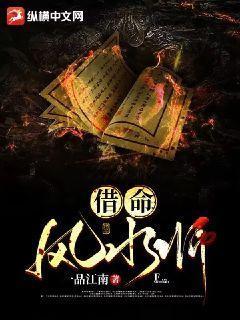秋天小说>深陷天龙人的包围圈 > 1620(第32页)
1620(第32页)
对于没有能力的O而言,确实也是不错的饭碗,毕竟大部分Alpha都很挑剔,结婚对象再怎么样也要是个干净的O。
即使标记能够洗去,不算上洗去标记要遭受的痛苦,被彻底标记过的O在相亲市场上都是劣质品。
几乎所有人都默认,愿意和劣质品Omega结婚的Alpha一定也是个不怎么样的Alpha。
所以,哪怕一个Alpha穷的只能捡垃圾了,也要娶一个干净的Omega老婆。
这就导致更多Omega流入黑色市场。
好[哔]的世界。
完球,惹上疯子了。
我:“这个试验开始的日期,可以由我来决定吗?”
坎贝尔:“当然,一切由时一同学来决定。”
坎贝尔把主动权交给了我,他要是Omega该多好,那样就不止能X一次了。
我一边感动落泪一边在心里权衡该什么时候开始确认具体该什么时候开始在坎贝尔身上做练习,肯定得是在校期间内。
还要留出时间去医疗舱里把痕迹修复掉,这样去搞傅镇斯的时候才不至于打哆嗦。
傅镇斯粗重的呼吸声起伏了瞬,他弯着背,迷彩色的背心上,肌肉隆起,线条分明,在病房门口摆弄了一会儿手里的摄像机,三下五除二搞定,推开门,“怎么不关门?”
谢枕弦回答道:“李家少爷,噢,现在是掌权人了,刚刚来过,说自己和时一是好朋友,带来了贝内特家族的慰问,他身体不适不能来,所以李家少爷一并带了过来。”
病态的面容变得更加苍白,发间多了一抹银丝,“他发现时一对他也没有反应……可能走的时候没有把门关好吧,哈,谁知道呢。”
“哦。”傅镇斯把恢复了初始设置的摄像机摆在了她的身侧,她没有反应,傅镇斯又推了推,贯穿了全脸的疤痕看起来很恐怖,她下意识地瑟缩。
傅镇斯看着她身侧的摄像机发呆,谢枕弦问他在做什么,傅镇斯平静地解释:“她旁边留下的只有一个毁坏的摄像机,我以为她会喜欢。”
谢枕弦搓了搓自己的太阳穴,疲惫地摘下平光镜:“她要是能对这个有反应,那早就该在我告诉她我除了她以外还有第二个弟子以后就有反应了。”
末了,他又道:“或者在我当着她的面帮她签审判官选举申请书的时候,也该有反应了。”
傅镇斯沉默了瞬,说道:“你还是没有死心?”
谢枕弦戏谑道:“死心这个词和我沾边吗我就死心?她想做,那就等到最后一刻,不是还有8小时,不到最后三十分钟,资格就不会被取消。你先死心行不行,你个老牛吃嫩草的糟心玩意,呵。”
他起身拎起饭桶去洗。
饭都是他做的,他怎么可能先死心,傅镇斯摇了摇头,掏出了两根棒棒糖,一根塞到了她的嘴里,一根进了自己的嘴里。
我头疼欲裂地收拾好自己,边思考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边去悬浮列车车站等车,上了车又开始思考具体的实施方案。
既然他回来过,还是带着其他人回来的。
那么今天晚上也会回来。
即使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是回来。
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我。
那么该如何把证据甩在他们面前,还能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及时让自己醒过来呢,经过昨天晚上的试验,我的熬夜极限是两点,超过两点就不行了,我这具身体可不是上辈子通宵三天三夜拍新闻稿也嘛事没有吃嘛嘛香的的好身体,是会自动关机的。
关机久了不知道哪天就真的醒不过来了。
赌不动,没资本赌,要找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如果有一台定时相机就好了,现在的科技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问题是怎么搞到?
“小——小时,啊!你黑眼圈怎么这么大!”方辞廖的声音犹如平地一声雷在我的耳畔响起,脑子瞬间清醒,我问他怎么今天突然坐悬浮列车了,他说自己的悬浮板被送去保养了,这段时间都要坐悬浮列车出行了。
万恶的有钱人,不坐自己的私家悬浮车跑来坐悬浮列车来和老人家抢位置。
虽然我看到老人来了也不会让座就是了。
我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把人盯得不好意思坐立难安了起来才移开目光。
相机的事情或许……
不行不能找他借。
不是利用太多愧疚的问题,是他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