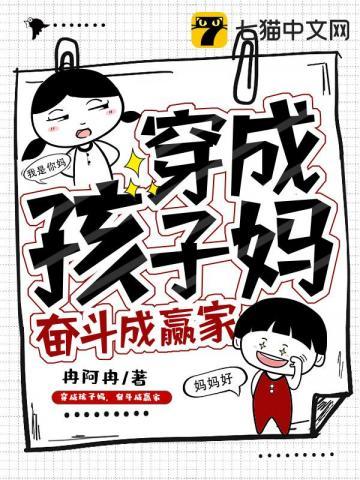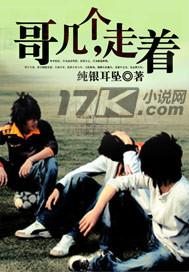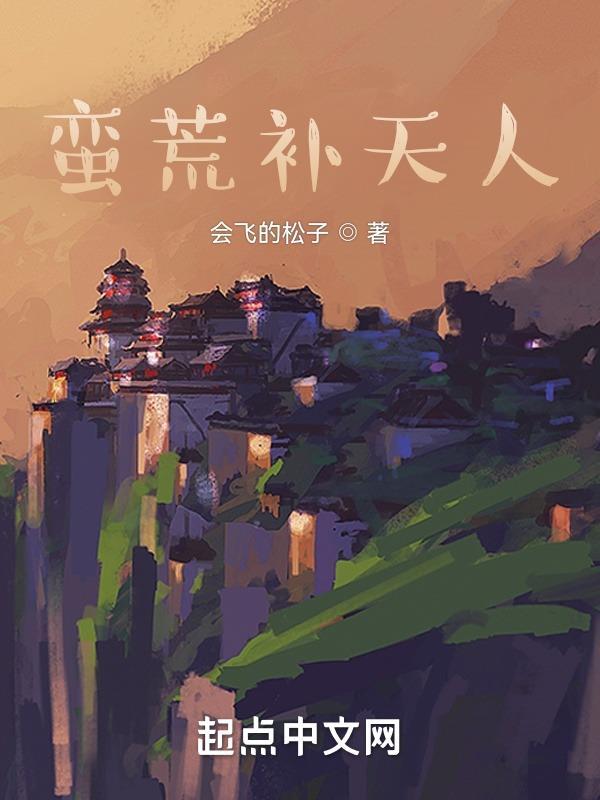秋天小说>嘉靖榜眼:从流放地到内阁 > 第9章 砚之应条件批县学作业(第1页)
第9章 砚之应条件批县学作业(第1页)
县学的晨读声穿透薄雾,在青砖铺就的庭院里回荡。沈砚之背着布囊,踩着未化尽的积雪,准时出现在县学门口。今日是他按约定来批改作业的日子,布囊里除了笔墨纸砚,还装着昨晚熬夜整理的《论语》批注——他想趁批改作业的机会,把自己对圣贤书的理解,悄悄分享给县学的弟子们。
“沈兄,你可来了!”书童小墨早就候在门口,见他来,连忙迎上去,手里捧着一摞叠得整齐的八股文稿纸,“刘先生说,这些都是弟子们昨日写的《论语》题作文,让你先看着,有不懂的地方,再去书房问他。”
沈砚之接过文稿,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心里泛起一丝暖意。这些文稿上还留着墨香,有的字迹工整,有的却略显潦草,能看出弟子们写作时的不同状态。他跟着小墨走进讲堂,里面空无一人——弟子们都去后院背书了,只有阳光透过窗棂,在书桌上映出斑驳的光影。
他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将文稿摊开,拿起毛笔,先仔细读起第一篇。这篇作文的题目是“吾日三省吾身”,作者是县学弟子李三儿。李三儿家境贫寒,却格外刻苦,只是每次写八股文,总在“破题”上犯难,要么流于俗套,要么偏离题意。
果然,这篇作文的破题写得平平:“夫三省者,乃每日自省也。”沈砚之皱了皱眉,提笔在旁边批注:“破题当点出‘省’之核心——非仅‘自省’,更在‘知过而改’。若只言‘自省’,未提‘改’字,便失了曾子立言本意。”
他又往下读,看到文中引用“颜渊问仁”的典故时,竟将“克己复礼”误记为“克己复理”,连忙用红笔圈出,批注道:“‘礼’者,周公所制之典章制度也;‘理’者,程朱所论之天理也。此处当用‘礼’,误用‘理’则失却原典,需谨记圣贤之言不可妄改。”
写完批注,沈砚之没有立刻换下一篇,而是对着文稿沉思片刻。他想起自己初学八股时,也曾犯过“破题不深”“引典有误”的错,还是父亲用“逐字拆经”的方法,教他把每一句圣贤言拆成字、词、意,才慢慢摸到写作的门道。或许,他可以在批注里,把这种方法悄悄教给李三儿。
于是,他又添了一行小字:“若遇经义题,可先将题目拆为三字:‘吾’(谁省)、‘日’(何时省)、‘三省’(省什么)。逐字拆解后,再结合自身经历立意,文章便有根了。”
写完这篇批注,沈砚之抬头望向窗外,见弟子们正背着书从后院走来,为首的正是李三儿。李三儿手里捧着《孟子》,边走边念,眉头紧锁,像是在琢磨某个难句。沈砚之放下笔,对着他笑了笑,李三儿愣了一下,也连忙拱手回礼,眼神里带着几分敬佩——昨日刘先生己经跟弟子们说了,沈砚之虽是“罪臣之后”,却有真才实学,连先生都赞他对《论语》的理解独到。
“沈兄,你批得怎么样了?”刘崇文不知何时站在讲堂门口,手里拿着一卷《朱子语类》,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我刚听小墨说,你在批注里教弟子‘拆题’之法?”
沈砚之心里一紧,连忙起身:“先生,晚辈只是觉得,弟子们或许需要更具体的方法指导,便斗胆在批注里提了几句,若是有不妥之处,还请先生责罚。”
“责罚倒不必。”刘崇文走进来,拿起那篇李三儿的文稿,仔细看着沈砚之的批注,嘴角渐渐露出笑容,“你这‘逐字拆题’之法,倒是比我教的更细致。我以前总跟他们说‘破题要深’,却没教他们怎么‘深’,你倒是帮我补了这堂课。”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你要记住,批改作业时,既要指出错处,也要留几分情面。这些弟子大多年轻,若是批注太苛责,怕是会伤了他们的志气。”
沈砚之连忙点头:“晚辈记住了。晚辈会在指出错处的同时,多写鼓励的话,让弟子们知道,只要改进,就能写出好文章。”
刘崇文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往外走:“你继续批吧,中午留在这里吃饭,我让厨房多做两个菜。”
看着刘崇文的背影,沈砚之松了口气,重新坐回书桌前,拿起第二篇文稿。这篇是弟子王富贵写的,王富贵是宁安县乡绅之子,家境优渥,写字也有几分天赋,只是文章里总带着一股“骄气”,动辄引用生僻典故,却不懂得融会贯通。
比如文中写“学而不思则罔”,他竟引用了《汉书》里的典故,与《论语》本意相去甚远。沈砚之在旁边批注:“引典当‘切题’,而非‘炫博’。此处论‘学与思’,当引《论语》内‘温故而知新’等句,若硬搬《汉书》,便如穿凿附会,失了文章本真。且君家虽富,治学当以‘谦’为先,若带骄气,纵有天赋,亦难成大器。”
写完,他又觉得“亦难成大器”一句太过严厉,便在后面添了一句:“若能戒骄戒躁,潜心琢磨,日后必能写出锦绣文章。”
不知不觉间,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沈砚之批完最后一篇文稿,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抬头却见讲堂里站着几个弟子,正偷偷看着他手里的文稿,眼神里带着好奇。为首的正是李三儿和王富贵。
“沈兄,我们……我们能看看您的批注吗?”李三儿犹豫着开口,手里紧紧攥着衣角,“先生说,您的批注里有很多治学的窍门,我们想学学。”
沈砚之笑了笑,把文稿递过去:“当然可以。只是我水平有限,批注里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你们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