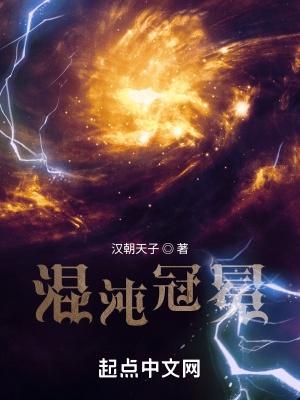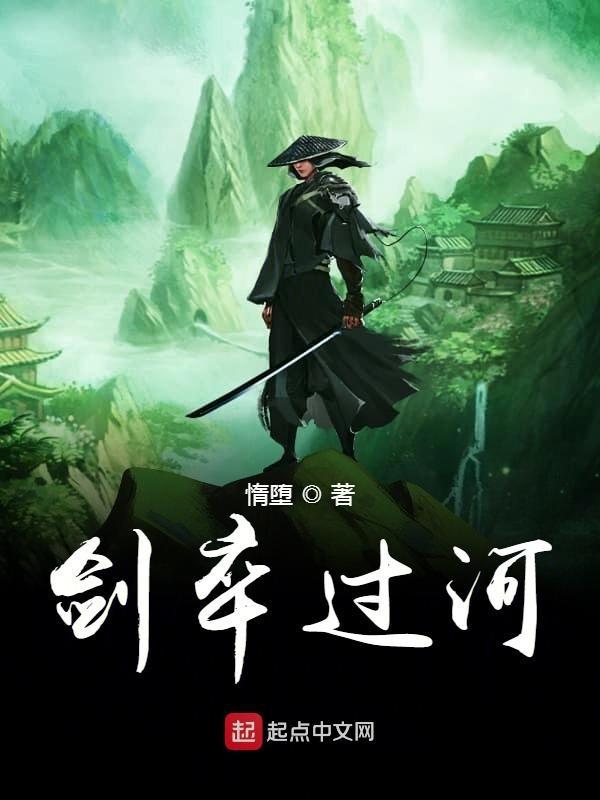秋天小说>骟猪工 > 9秀梅五(第2页)
9秀梅五(第2页)
大家拿出的东西不多,但琐碎。她每样都记下,写好后又挨个对了一遍,确认没有没有问题后,又拿出一张纸誊抄了一遍。
一式两份,一份放她这,一份放丽娟那。
之后还要把纸上的物件都挨家还回去,马虎不得。
写下最后一个字,她捏了捏酸胀的眉心。人老了,确实不比当年,字稍写小点就费神。
“丽娟。”她将一份叠得方正,交到郑丽娟手里,“总共三十五块八毛六,你怎么打算?”
“十块米面,十块菜肉,十块日常花,剩下的五块八毛六就当应急,真出事了还有笔钱能用。”
周韵有点担心:“十块米面怕是不够。”
“够用,你忘了我是干啥的?”郑丽娟将纸贴身放好,“我店里新鲜的大米不多,但陈米不少,本来也卖不出去,正好这次能派上用场,够大家吃三天的,就是味道不大好。”
树皮都吃过的人哪会嫌弃陈米,周韵盘算着:“新米给那几个还在长身体的女娃娃吃,咱们吃陈米就行。菜的话,可以去地里山上摘点野菜,肉乔壮说可以半价卖给咱。三天,够咱们赚到钱了。”
周韵作为村里女人的领头人,知道各个女人的技能,很快就给每个人安排好了岗位。
年纪大的如吴晓霞这类,别看好像除了种地外没其他技能,但她们资历深厚,对村里的土地了如指掌,知道哪块地上长着什么野菜,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还知道野菜怎么炒最好吃。这片土地孕育了她们,她们也将土地的痕迹刻进皱纹和厚茧里。
稍年轻点嘴甜会说话的,如郭香仪之类,就跟着郑丽娟去城里,售卖村里女人自制的小物件:竹篮、扫帚、鞋垫……要是能帮着接点缝补浆洗的活,就更好了。
其他女人则按照自己会的,依次分成几个队伍,再从队伍里各选一个负责人出来。负责人不但要干活,还要记录自己队伍里各人员的干活情况,每晚都要向周韵汇报。赚的钱会集中用来返还之前大家拿出的钱,要是有剩余,就按照每个人干了多少依次分配。
在这个偏僻、落后又封建的小村庄里,女人们靠着对彼此的信任,对利益的共享,对公平的追求,自己形成了一套模糊但超前的,包含公有制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思维的经济制度。而距离真正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确立,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女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如今的想法有多开天辟地,她们在分完组后,看着呆呆站在中间的女人犯了难。
“妹子,你有啥会的不?”周韵不知道她叫啥,村里的男人都随老小子叫她“一千三”,因为她被卖到村里时,老小子花了一千三买下她。但村里的女人从来不这么叫,真要论买卖,村里又有哪个女人不是男人们买卖来的。
女人张着嘴咿咿呀呀地比划了一顿,见没人听懂,她有些急了,她怕不干活被赶回去,到时怕真要被老小子给活活打死。
“啊——”她指着周韵手里的纸,又用指头在空中划了划。
周韵眼睛一亮:“你会写字?”
“嗯!”她重重点了点头。
“居然会写字!”围观的女人顿时炸开了锅,在她们看来,会写字的女人都是有大出息的。像周韵,像乔壮的阿姊,就连只会识字的郑丽娟都是村里的厉害人物。
像是怕她们不信,女人连忙从鞋垫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动作小心地摊开,放在众人面前。
纸上的字早已被泛起的白痕拆成黑点,周韵眯着眼仔细辨认,才发现是“秀梅”两个字。
“你叫秀梅?”
“嗯!”女人点点头。
“姓什么?”
“嗯……”女人摇摇头。她被卖来的太久,对自己的存在和认知,早已在一声声的“一千三”和毒打中模糊。
“想不起来也没事,以后我们就叫你秀梅了。”周韵将她的纸小心地折好,翻动间,正好看到最上头的五个大字,手一抖,失声叫了出来。
“入学通知书!你是大学生!”
大学生?秀梅迷茫地看着那张发黄的、长满白斑的纸。
她是大学生吗?
记忆中两个看不清模样的女人围着她转圈、大叫、哭泣,她想不起她们的脸,却下意识抬手想擦去她们的泪。
她举起和田间泥路一样粗糙的手指,按在那不再鲜艳的大字上。
对啊,她是出门去上大学的,怎么会在这啊。
一颗一颗咸涩的水珠打在纸上,秀梅像是被人按进水缸里,周围的声音化作咕噜噜的水泡,听不真切。她喘不上气,只能一遍又一遍摸着那被水珠泡软晕开的黑字。
不对啊,她是出门去上大学的,怎么会在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