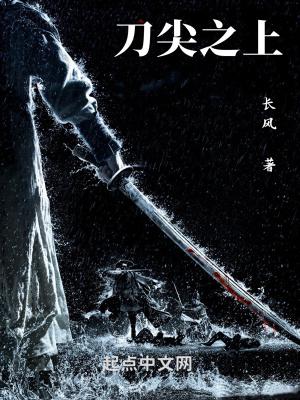秋天小说>平生有所遇【鬼灭之刃】 > 第 15 章(第2页)
第 15 章(第2页)
终于,她抬起头,脸上重新浮现出那抹熟悉的、浅浅的微笑。但这一次,那笑容里没有了往日的距离和公式化,而是带着一种深深的、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的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释然。
“茶凉了。”她轻声说,然后端起我面前那杯早已不再冒热气的茶,将冷掉的茶汤缓缓倾倒在旁边的茶洗中。然后,她重新拿起水壶,注入滚烫的热水,再次为我斟满了一杯,推到我面前。
“蝶屋的规矩,”她看着我,紫色的眼眸中似乎有微光流转,“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前来投奔的人。”
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狂喜和更深沉的酸楚瞬间淹没了我。泪水终于决堤,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我慌忙低下头,不想让她看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
一只微凉的手,却轻轻地、带着些许迟疑地,覆上了我紧紧攥着拳头、放在膝盖上的手背。
我浑身猛地一颤,难以置信地抬头。
忍的手并没有停留太久,只是轻轻一触,便收了回去,仿佛那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但她耳根处,却泛起了一抹极淡的、在夕阳余晖下几乎难以察觉的红晕。
“既然留下了,”她的声音恢复了一贯的平静,却少了几分清冷,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温和,“就要遵守蝶屋的规矩。不许……再擅自离开。”最后几个字,她说得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嗯!”我用力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声音哽咽得说不出更多的话。暮色四合,廊下点亮了温暖的灯笼。紫藤花的香气在夜晚的空气中愈发浓郁。我们相对而坐,她沉默地喝着那杯重新沏好的、带着暖意的茶。没有人再说话,但一种无声的、沉重而温暖的谅解,仿佛随着茶香,缓缓流淌在我们之间。
------------------------------------------------------------
留在蝶屋的日子,像是一卷被拉长了的、浸透着苦涩药香与隐秘微光的丝绸。每一天都从清晨开始,在忍踏入病房的脚步声中有序地展开。我被安置在最初那间僻静的屋子,窗外是茂盛的花,阳光透过花叶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对我而言,那光是危险的,也是诱惑的,时刻提醒着我的身份和界限。
当初被阳光灼伤的左手日日传来疼痛,哪怕是鬼也无法复原,于是,忍执行着医士的职责为我探寻治疗的可能。
忍每日都会准时出现,进行例行的检查与换药。她的到来总是伴随着那股清冽的药草气息,脚步轻盈,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规律性。最初的几天,我们之间的空气总是凝滞的。她脸上挂着那副近乎完美的、带着距离感的微笑,动作精准、利落,清洗、消毒、上药、包扎,每一个步骤都如同最精密的仪器,不带一丝多余的情感。
她会询问我伤口的愈合情况,鬼化身体对药物的反应,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记录一份寻常的病案。我则总是垂着眼,简短地回答“还好”、“没有异常”,不敢过多地注视她,生怕从那紫色眼眸中看到一丝厌恶或怜悯。
但变化,总是在最细微处悄然发生。
有一次,她为我检查左臂重生处的愈合情况时,指尖无意中触碰到我新生的、异常敏感的皮肤。那冰凉而轻柔的触感,让我控制不住地战栗了一下。她的动作微微一顿,抬起眼帘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似乎闪过一丝极快的、难以捕捉的情绪,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但接下来的动作,却明显放得更轻、更缓了些。
又一天,她带来了一种新调配的药膏,说是可以缓解鬼化躯体在阳光下残留的灼痛感。她亲自为我涂抹在那些被阳光灼伤后留下浅淡痕迹的皮肤上。药膏带着薄荷般的清凉,她的指尖蘸着药膏,一点点推开,力道适中,避开所有可能引起不适的区域。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我也屏住呼吸,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轻微的呼吸声和药膏涂抹时极细微的摩擦声。那沉默不再令人窒息,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令人心安的专注。
除了治疗,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交谈。但偶尔,在换药结束后,她不会立刻离开,而是会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紫藤花,状似无意地提起一些事情。)“炭治郎那孩子,恢复得很快,已经开始进行基础训练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伊之助今天又把训练场的木桩撞坏了一个。”她会微微摇头,嘴角似乎有极淡的、真实的无奈弧度。“香奈乎……她很有天赋。”提到她的继子时,她的语气会带上一种不易察觉的柔和与期许。
她从不直接问我什么,也不谈论关于鬼、关于斑纹、关于未来的任何沉重话题。这些看似琐碎的、关于蝶屋日常的只言片语,像是一颗颗小石子,轻轻投入我们之间沉默的深潭,漾开一圈圈微小的涟漪。我渐渐明白,这是她独有的、表达“接纳”与“靠近”的方式——她在将她所守护的这个世界的一角,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展露给我看。
而我,也开始尝试着做出回应。虽然依旧笨拙,依旧带着怯懦。我会在她提起炭治郎时,低声说一句:“他很有毅力。”会在她说起伊之助的莽撞时,忍不住轻轻弯一下嘴角。甚至有一次,当她提到香奈乎学习某种复杂药方遇到瓶颈时,我鼓起勇气,根据自己早年受伤时积累的粗浅药草知识,提出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关于药材处理顺序的建议。我说得磕磕绊绊,说完就后悔了,觉得自己班门弄斧。忍却意外地没有反驳,也没有露出任何不屑的神情。她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紫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光亮:“这个角度……倒是未曾细想。或许可以一试。”
那一刻,一种微小的、几乎不敢置信的喜悦,悄悄在我心底蔓延开来。我们的相处,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白天,她是严谨的医者,我是需要照料的特殊病人。但到了夜晚,当蝶屋彻底安静下来,有时,我会听到极其轻微的脚步声停在门外。她没有进来,只是静静地站一会儿,然后离开。我知道那是她。她在确认我的存在,确认我没有再次消失。而我,则会在她离开后,悄悄走到门边,隔着纸门,感受着那残留的、令人安心的冷香,不愿离去。
最让我心弦震颤的一次,是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因为鬼化后增强的听觉,隐约听到远处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是忍的声音。那咳嗽声带着隐忍的痛苦,让我瞬间揪紧了心。她体内的紫藤花毒素……终究是在反噬她的身体。我几乎要冲出门去,但最终还是死死忍住了。
第二天清晨,她来换药时,脸色比平日更苍白几分,但笑容依旧完美无瑕,动作也一如既往地稳定。只是在调配一种安神药剂时,她的手几不可察地微微颤抖了一下。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扶住那个快要滑落的药瓶,却在指尖即将触碰到她手背的瞬间,猛地缩了回来。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动作,抬起眼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辨,有疲惫,有隐忍,或许还有一丝……极淡的、被压抑的波动。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药剂调配完成。
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仅仅是人鬼的界限,更是她那份与自身命运抗争的、孤独而决绝的意志。我无法分担她的痛苦,只能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守在她必经的路旁,用我这不死的生命,去见证、去铭记她燃烧的每一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过,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秋日肃杀的气息逐渐浓稠,连蝶屋的空气都似乎变得粘滞起来。一个消息在幸存的队员间悄悄传开——山脚下那个在无限城灾难中侥幸存续的小村庄,为驱散阴霾、庆祝新生,决定在今晚举办一场烟火大会。
炼狱杏寿郎大哥得知后,他那洪亮的嗓音立刻响彻了整个蝶屋廊下:“大家一起去!”
他的提议得到了炭治郎、善逸、伊之助这群少年人最热烈的响应,连一向不喜不死川实弥也只是哼了一声,并未反对。富冈义勇沉默地点了点头。一种久违的期待,开始弥漫。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和忍这里。当时,她正在为我更换手臂上最后一点绷带,动作依旧轻柔专业。我低着头,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微顿,以及随后更加刻意的平稳。
我并不想去,方从鬼所造成的恐慌中恢复不久的世界实在不适合再次出现一只鬼。
然而香奈乎送来浴衣时,我还是心动了。
我渴望重新与这个世界建立新的联系,不只是和忍,不只是和蝶屋,甚至是和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