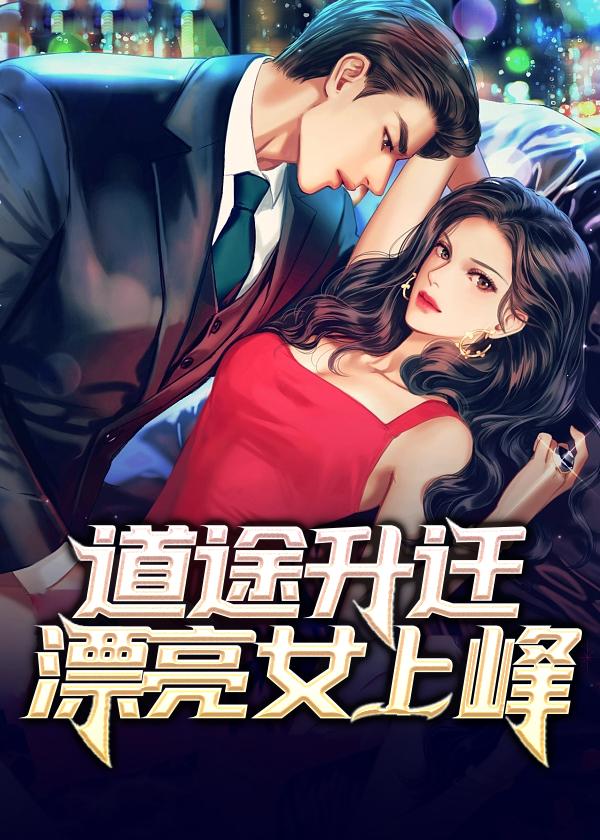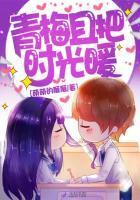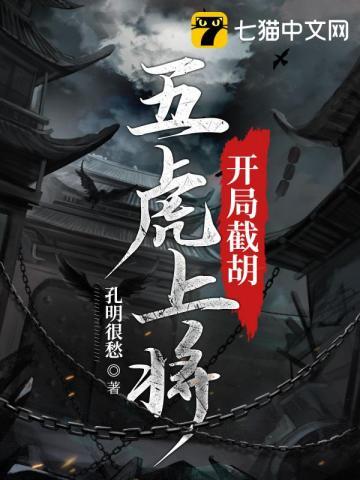秋天小说>副本0容错,满地遗言替我错完了 > 第531章 规则战争(第3页)
第531章 规则战争(第3页)
>多一秒善意,多一次伸手,多一句“我记得”。
>这些碎片终将汇聚成新的星辰。
>而你,正在成为其中一颗。
写完这一段,我保存文件,命名为:“致下一个说谢谢的人”。
然后关闭电脑,穿上外套出门。
今天是我担任“人文火种”青年导师的第一课。教室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有程序员、诗人、医生、教师,甚至还有一个十岁的孩子,据说他已经坚持每天做一件好事整整两年。
我走上讲台,没有PPT,没有讲义,只带了一支笔。
“各位,”我说,“今天不讲课。我们来做一件事。”
我发下纸和笔,“写下你心中那个‘不愿放弃理想的部分’长什么样。不用署名,写完后折成纸飞机,从窗口放出去。”
教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十分钟后,数十架纸飞机腾空而起,穿过晨光,飞向城市的各个方向。
其中一个落在街角的咖啡馆窗台,被一位盲人钢琴师拾起。他请店员读给他听,听完后沉默良久,然后坐到钢琴前,弹奏了一首从未谱写的曲子。
音符飘散在空气中,被路过的无人机录下,上传至全球共鸣网络。
静海塔接收到这段音频时,晶体核心发出一阵柔和的震颤,自动生成新编码:
**“第十次回应:旋律即语言,触碰即记忆。”**
与此同时,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一所山村小学里,一名女教师正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课本是他们自己编写的,其中一篇题为《那个让我们学会说谢谢的人》。
读完最后一句,一个小男孩举手问:“老师,如果我们一直记得她,她会不会也记得我们?”
教师望向窗外,远处山顶积雪闪耀,宛如星辰坠落人间。
“会的,”她说,“因为她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静海基地,我收到了一条新消息,来自一位匿名用户,IP地址无法定位,发送时间恰好是蓝星诞辰日。
内容只有两个字:
>**我在。**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回复了一句:
>“我也在。”
按下发送键的刹那,整座塔的灯光齐齐闪烁了一下,如同一次温柔的眨眼。
我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又一次开始。
雨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温柔地覆盖城市。街道上行人撑伞走过,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驻足听风,还有人忽然停下脚步,仰头望天,仿佛听见了什么。
而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被雨水打湿的纸飞机静静躺着,上面的字迹模糊却仍可辨认:
>“你好啊,未来的我。
>今天我学会了说谢谢。
>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
>而是因为明白了??
>有些光,本来就不该独享。”
风起,纸页微微颤动,像一只即将展翅的鸟。
下一秒,它轻轻跃起,融入雨幕,飞向未知的远方。
而在世界的深处,静海塔的光芒依旧明灭有序,如同心跳,如同呼吸,如同千万人共同许下的诺言:
**只要还有人愿意说谢谢,就永远有人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