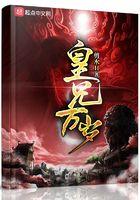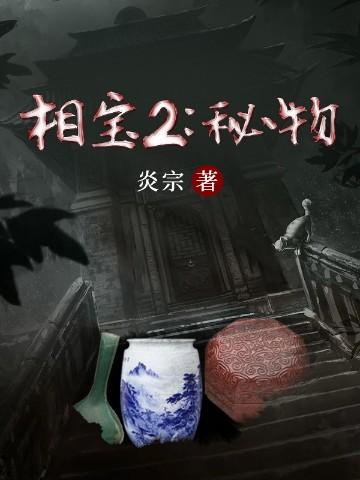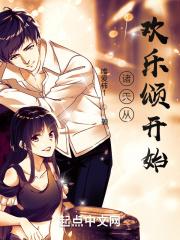秋天小说>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06章 五个女人一台戏绿茶(第1页)
第606章 五个女人一台戏绿茶(第1页)
卡萨布兰卡,北边郊外的一个小镇。
小镇中心街道的三条街道上。
这里铁丝网,沙袋遍布,各种掩体后架设着机枪等武器。
还有不少的美制悍马车,法制VAB轮式步战车,苏式坦克等装备。
。。。
林浩然把那杯奶茶放在篝火边的石台上,没有再喝。他看着火焰跳动,映在眼底像一簇不肯熄灭的执念。夜风拂过,火星子随气流升腾,转瞬融入星空,仿佛某种无声的传递。学生们陆续散去,有的回屋整理素材,有的抱着吉他坐在院角轻声哼唱。周小雨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你猜我今天翻到了什么?”她低声说,“是赵建国出狱前写的最后一段日记。”
林浩然侧头看她。火光下,她的眉眼柔和得像是被岁月轻轻抚平了棱角。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儿子面前,不再用道歉开场,而是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要不要一起去吃碗面?’”周小雨念完,声音微微发颤,“就这么一句话,他写了七遍,划掉六次。”
林浩然闭上眼,喉结动了动。他知道那种小心翼翼,那种怕连最普通的亲近都显得冒犯的心情。他曾无数次在镜头前扮演别人的人生,却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最艰难的台词,往往不是慷慨陈词,而是一句轻如尘埃的日常问候。
“我们拍下来吧。”他睁开眼,“不采访,不摆拍,就跟着他们,从早上起床开始,记录一天的生活。哪怕什么都没发生,也值得留下。”
周小雨点头:“我已经联系了绵阳那边的民宿,可以住下。只是……你要确定,这还是‘回音计划’该做的事吗?有人会说这是窥私,是消费亲情。”
“那就让他们说。”林浩然站起身,走到火堆旁捡起一根枯枝拨了拨炭灰,“我们不是在拍父子和解的戏码,而是在见证一个普通人重新学习做父亲的过程。就像古丽娜尔的学生想当一天城里人一样,赵建国也只想当一天普通的爸爸??这个愿望够卑微了吧?可对有些人来说,它比登天还难。”
第二天清晨,他们启程前往绵阳。车行至半路,接到消息:赵建国已按儿子留下的地址,独自去了其中一个工地,帮几个被骗工资的工友写了诉状,并联系了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对方起初不信他,直到看见那份《愤怒日记》的样书,有工人当场红了眼眶:“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过。”
林浩然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描述,久久无言。他忽然意识到,这些故事早已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它们正在彼此缠绕、生长,形成一张看不见却坚韧的情感网络。一个人的声音落地,另一颗心便悄然松动。
抵达绵阳当晚,他们并未打扰赵建国父子,只在附近租了间民房安顿下来。第二天一早,林浩然带着摄像机悄悄跟去工地。赵建国穿着洗旧的工装裤,蹲在水泥地上教几个年轻工人如何写欠条、保留证据。阳光刺眼,他额头上沁出汗珠,说话时手势很稳,语气平和,像个真正的老师。
镜头远远地拍着,没靠近。直到中午收工,赵建国拎着两个饭盒走向宿舍楼,林浩然才慢慢跟上去。
“爸。”门口站着那个年轻人,接过饭盒时第一次叫出了这个称呼。
赵建国愣了一下,手微微抖,随即点了点头:“嗯。”
两人并肩走进狭小的房间,墙上贴着几张建筑图纸,床头放着一本翻烂了的《劳动法释义》。吃饭时谁也没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吃完后,儿子突然问:“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酸辣粉吗?”
赵建国抬头看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惊疑:“东街口那家?老板姓张,总多给你一勺花生?”
“对。”儿子低头收拾碗筷,“今天关门了。”
空气静了一瞬。然后赵建国轻声说:“我记得那天你发烧还非要吃,我背你走了两公里……路上摔了一跤,汤洒了,你还笑。”
儿子停住动作,背对着他,肩膀微微耸动。
林浩然站在门外,没进去,也没关掉机器。他知道这一刻不该被打扰,但他也知道,若没有这台机器,也许这份记忆永远无法被完整保存。有些话,需要媒介才能抵达终点;有些爱,必须借由凝视才能确认存在。
三天后,他们决定拍摄一场真正的“普通日子”。没有预设情节,不做任何引导,只是记录赵建国和儿子一起买菜、做饭、散步的过程。早晨六点,两人骑一辆二手电瓶车赶集。菜摊老板认出赵建国,笑着说:“又是你啊,昨天买的土豆炖烂了吗?”赵建国答:“烂了,但好吃。”儿子在一旁抿嘴笑了。
他们在河边摊煎饼,风吹乱了头发,油锅滋啦作响。回家路上,儿子主动提起要修家里坏掉的热水器。“你歇着吧,”他说,“我能弄。”赵建国站在旁边,看着他蹲在地上拆零件,手心里攥着扳手,指节泛白,像是怕自己伸手就会吓跑这一刻的平静。
晚饭时,儿子忽然说:“我想报名成人高考。”
赵建国夹菜的动作顿了一下:“想考什么?”
“建筑工程管理。”
“为啥?”
“我不想一辈子绑钢筋。”
赵建国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那你得补数学。我可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