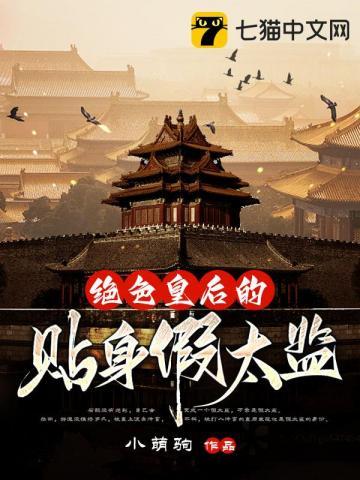秋天小说>青袍映沧澜 > 春和她胸有丘壑(第2页)
春和她胸有丘壑(第2页)
公孙止缓缓摇头,那深潭般的眼眸里,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出名为“惋惜”的情绪,浓重得化不开。
“如鱼得水?”他重复了一遍,带着一丝冷峭的意味。
公孙止:“或许在旁人看来,她将萧家产业打理得蒸蒸日上,深得太子倚重,离那母仪天下的位置仅一步之遥,自然是风光无限,得偿所愿。”
可说完那番后,公孙止停顿片刻,目光落在扶登秦脸上,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锐利:“但秦儿,你跳出与她针锋相对的立场,细看她今日言行举止,可曾觉得……像?”
扶登秦一怔,脑海中瞬间闪过萧春和的身影:
那身天水碧云锦长裙一丝不苟的剪裁,发髻上价值连城的羊脂白玉簪,耳畔恰到好处的珍珠坠子,连踩着昂贵毡毯下车的姿态都像是精心计算过角度,力求那份“白鹤涉水,不染纤尘”的完美仪态。
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像是照着“未来太子妃”、“贤内助”的模板,精准复刻出来的。
“像……”
扶登秦喃喃道,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带着同为女子的敏锐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悲哀。
扶登秦:“像一幅……画。一幅工笔细描、价值连城、却失了鲜活神韵的仕女图。她在模仿,模仿她认为‘应该’成为的样子——端庄、得体、明理、识大体、永远将‘大局’置于个人情感之上,甚至置于人命安危之上。”
她想起萧春和扫过自己与公孙止时那几不可察的蹙眉,那眼神并非厌恶,更像是在审视一处有碍观瞻、需要尽快清理的“不整洁”。
那份高高在上的疏离感,并非天生贵气,更像是后天精心打磨出的保护壳,或者说……伪装。
扶登秦:“先生当年赞誉她‘有入阁拜相之能’。”
“如今看来,这份‘能’,全数化作了替太子权衡利弊、掌控财源、甚至……粉饰太平的‘能’。”
“她将自己活成了太子手中最锋利也最称手的一把算盘,每一颗珠子拨动,都精准地落在‘利’字之上。”
“那份曾让先生也为之侧目的、属于萧春和本身的肆意锋芒与鲜活心智呢?是否早已在日复一日模仿‘贤良淑德’、计算得失盈亏中,被磨平了棱角,锁进了深闺?”
公孙止静静听着扶登秦的话,没有反驳。
他看着帐外阴沉的天色,仿佛看到了当年云山书院后山,那个因辩论获胜而笑得眉眼弯弯、不顾形象地坐在石阶上、衣袖沾了墨渍也浑不在意的少女。
那时的光芒,是发自内心的璀璨。
而今日工地上那个萧春和,周身笼罩的光华,却像她裙摆上的银线缠枝莲,是精心绣上去的,再耀眼,也失了那份源自灵魂的热度。
公孙止最终开口,声音低沉得如同叹息:
“模仿得久了,或许连她自己,也分不清那副完美的面具之下,是否还藏着当初那个萧春和了。所求为何?是那顶凤冠的重量,还是……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应该如此’中,忘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他看向扶登秦:“秦儿,你要的那个‘解释’,或许连她自己,也给不出了。”
帐内再次陷入沉寂。
甜羹的热气早已散尽,只留下温凉的瓷碗。
扶登秦看着碗中凝固的羹汤表面,仿佛看到了萧春和那层完美无瑕却冰冷坚硬的表象。
扶登秦所求太子的解释,是关乎人命与公理;而萧春和这个人本身,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令人扼腕的、关于“失去自我”的无声解释?
那支插在她发髻上的羊脂白玉簪,温润依旧,却像一道冰冷的封印,锁住了曾经可能翱翔九天的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