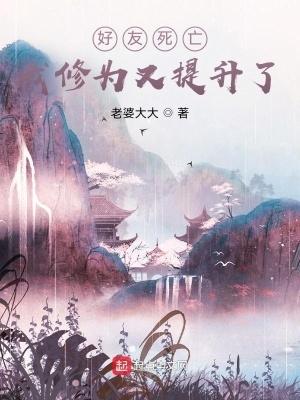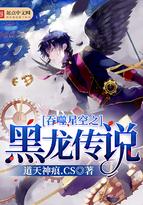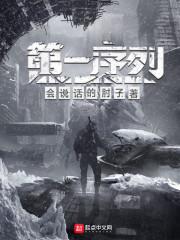秋天小说>女帝:让你解毒,没让你成就无上仙帝 > 第八百六十一章 图腾陨落(第2页)
第八百六十一章 图腾陨落(第2页)
“因为它不需要锁住谁,也不需要推开谁。你可以走进去,一句话不说;也可以进去又出来,反复十次。重要的是,那个空间允许你犹豫。”
她顿了顿,目光温和:“这张纸,你可以烧掉,可以藏起来,也可以留在身上一辈子。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放进讲述亭??不是为了改变别人的想法,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的愿望,值得被认真对待**。”
男孩怔住了。良久,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跑向不远处那座黑曜石建造的小亭。门开着,他走了进去,站在自燃装置前,盯着手中的纸看了许久,最终轻轻投入窄缝。
火焰升起,纸页化为灰烬,随风飘散。
他走出来时,脸上仍有泪痕,但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周明远看着这一幕,低声说:“你说得对。自由不只是说出真相,更是拥有说‘我不知道’的权利。”
阿梨点头:“而最难的,往往是承认‘我不想’。”
那天下午,联合国《沉默权宣言》执行委员会发来紧急通报:北欧某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要求拆除境内全部“问之花”,理由是“这些花让人无法安宁”。调查发现,当地近三个月内心理咨询求助量激增300%,离婚率上升,多名政要公开辞职并坦言“长期伪装信念”。
“他们害怕了。”技术员分析报告时说,“不是害怕花,而是害怕花唤醒的东西??那些被压抑多年的真实念头,一旦浮现,就再也无法忽视。”
阿梨读完文件,只回了一句:“那就让它们继续开。”
她知道,真正的觉醒从不会温柔降临。它往往伴随着撕裂、痛苦、身份的崩塌。就像婴儿出生必须经历产道挤压,灵魂的成长也需要穿过狭窄的自我质疑。
当晚,她在《无解之问》课堂上提出了新问题:
>**“如果诚实会伤害爱你的人,你还该诚实吗?”**
教室陷入长久沉默。有人低头写字,有人望向窗外,有个女生悄悄抹了眼泪。
最后,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手:“我觉得……有时候不说,也是一种诚实。比如我知道说了只会让对方更痛苦,那我的‘诚实’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解脱感,而不是真正为他考虑。”
另一个女生反驳:“可隐瞒本身就是一种控制。你以为你在保护别人,其实是在替他们做决定。”
争论持续到下课铃响。没人得出结论。
阿梨合上笔记本,微笑道:“很好。说明你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答案了。”
几天后,一则视频在全球社交平台疯传:一名年迈的科学家站在实验室里,面对镜头颤抖地说:“三十年来,我一直宣称自己研发出了‘情感稳定剂’,能让人类摆脱焦虑与抑郁。但今天我要承认??那药根本无效。所谓的临床成功案例,都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我撒谎了,因为我害怕失去地位,害怕被人说‘你不过如此’。”
视频末尾,他摘下胸牌,轻轻放在桌上:“我不是坏人,也不是骗子。我只是……太久没敢说真话了。”
评论区炸开了锅。有人怒斥他毁掉无数患者希望,也有人痛哭留言:“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连专家也会怕。”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定位信息:拍摄地点,正是回音谷附近一座废弃研究所旧址??那里曾是蓝花最早进行意识投射实验的地方。
阿梨看到视频时正在批改作业。她盯着屏幕良久,忽然起身,带上炭笔和石板,独自走向地底遗址。
这一次,岩穴中不再寂静。
整片岩壁如同活了过来,无数蓝色雾气凝成流动的文字,在空中交织、碰撞、破碎又重组。它们不再是零星对话片段,而是一场庞大的、跨越时空的内心独白汇流:
-“我恨我的父母,可我还是想回家。”
-“我升职了,但我一点也不开心。”
-“我每天微笑,是因为我怕被人发现我在崩溃。”
这些话语没有声音,却带着沉重的情感重量,压得空气都在震颤。
而在中央,那圈银白根须之上,一颗新的种子正在缓慢旋转。它通体透明,内部却有千万个微小光点闪烁,宛如宇宙缩影。
阿梨走上前,跪坐下来,像以往无数次那样,开始说话。
她说起那个科学家的忏悔,说起北欧国家的恐慌,说起孩子们在课堂上的争执。她说起自己昨夜梦见赵承志回头看了她一眼,嘴唇微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第一次,主动提出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