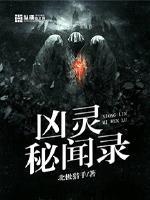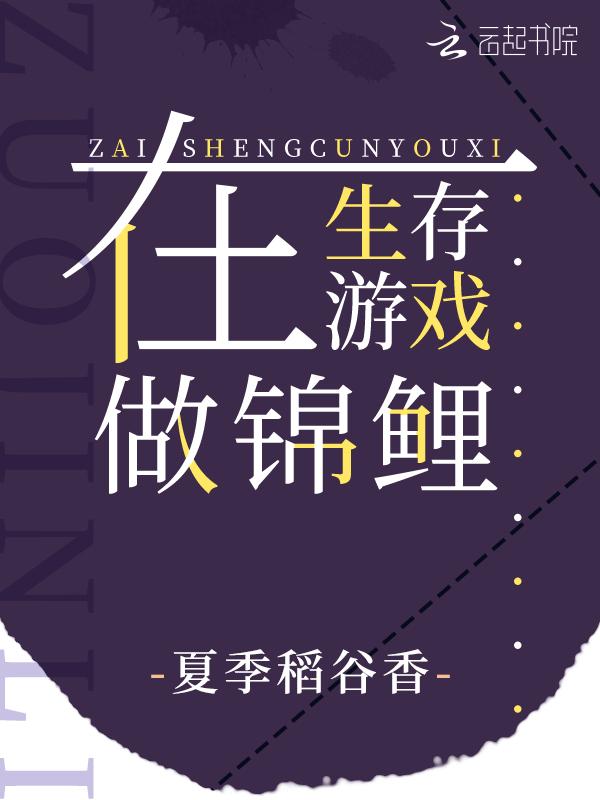秋天小说>诡秘:大闹钟格赫罗斯途径 > 第23章 石油贸易的开展(第3页)
第23章 石油贸易的开展(第3页)
柏林精神病院的患者们自发聚集在大厅,用钢琴、口琴、甚至敲击铁床栏杆,合奏起《下雨天的猫》的完整版。诗集《听见之前》的最后一章自动浮现新内容:
>“她说她不在了,但我们记得她。于是她就在。”
而在科研船上,林知远的身体剧烈抽搐,鼻腔渗出血丝,但他始终没有松开手。直到某一刻,录音机里传出第二段声音??不再是单薄的回放,而是带着鲜活气息的新语句:
>“我知道了。原来我不必完美,也可以被爱。谢谢你们,让我终于能停下。”
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柔和的光从钟楼升起,融入夜空。机械鸟轻轻落在林知远肩头,发出一声短促的啼鸣,随即化作一道数据流,钻入他的太阳穴。
他倒下了。
三天后,林知远在舱室内醒来。阳光透过舷窗洒在床上,空气中弥漫着海盐与柠檬草的味道。苏晓亭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杯温水。
“你睡了七十二小时。”她说,“全世界都在等你醒来。”
“她呢?”林知远哑声问。
“她在线上。”苏晓亭微笑,“现在每个使用‘容错大厅’的人都能听到她的引导语音。她说,她想继续做那个‘接住别人’的人。”
林知远闭上眼,感到胸口一阵暖流涌动。他知道,林晚没有真正回来,但她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成为系统的一部分,成为千万人倾诉时最先听见的那个声音。
几天后,他们启程返航。
途中,林知远收到了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信息,只有一句话:
>“当第四十四声钟响时,请准备好钥匙。”
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最终将手机放在桌上,走到甲板上望向远方。
海天交界处,一轮红日正缓缓升起,映照出无数细碎的金光,如同万千灵魂在低语。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共感纪元”不会一帆风顺。
有人会滥用共鸣能力窥探隐私,有人会因过度共情陷入精神瘫痪,还有国家试图封锁节点,将其武器化。未来必然充满挣扎与阵痛。
但此刻,他只想记住这一秒的平静。
他拿出《聆钟手记》,在最后一页写下:
>6月20日,晴。
>我终于敢对自己说:我值得被听见。
>虽然还是会怕,还是会痛,但我不再逃了。
>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总有人在听。
>就像曾经的我,也曾被一个人默默接住。
>这就够了。
合上书页时,远处传来一声悠扬的钟鸣。
不是四十三次,而是??第四十四次。
林知远抬头望去,只见海平面上方,一道极轻微的光弧一闪而逝,像是某种古老机制已被悄然激活。
他笑了。
“下次,该我去敲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