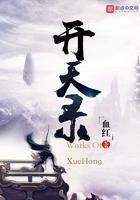秋天小说>豪商·女强 > 8090(第16页)
8090(第16页)
见她不似玩笑,张六郎老实道:“那边的东家当年听过我几出戏,同我本人不大熟,只我当初的好友去扬州做起一个戏班子,仍叫他捧场。”
又隐晦地问明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明月不确定他的话中有几分真,几分假,也不晓得那边的戏班子同那染料商亲密到何种地步,不便明说,只含糊道:“我连着两次同那边买卖,也不算小客了,又是亲自过去,竟还见不着他们东家的面……想来他贵人事忙,强求不得,不过也烦你托人时常帮忙打听着消息,我日后买卖且长久着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货全、量大又公道t的染料行,可千万别因为内斗解体了!
纵然真的斗起来,我也要先弄明白谁是最后赢家,然后再跟赢家做买卖。
张六郎听了,以为明月觉得那边只派出管事的接待,面子上过不去,当下顺着说了几句,“兵对兵,将对将,确实是怠慢了,既如此,我且托人看着,等什么时候他们东家在,也递个话……”
末了,张六郎亲自送她出门,并承诺扬州那边有动静会头一个告诉她。
明月稍稍放了点心。
只要张六郎说话算话,来日即便庞管事那边闹腾起来,自己也能先一步得到消息,不至于火烧眉毛才琢磨对策。
一点染料而已,竟这样一波三折,真是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接下来几日,明月都待在染坊,和朱杏、七娘一起琢磨新花色一事。
“流霞”与之前的“霞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个胚布是极轻极薄的纱,一个却是中等厚度的扎实的缎子,着色、用量大为不同。
朱杏上来就把染料用量减少一半,铰了一段湖纱试染,奈何还是重了:染料几乎糊住了轻纱的每一个孔洞,提出来晾干后竟成了硬邦邦的一整片,莫说轻盈灵动,摸着都有点扎手。
再减一半,染出来的不够鲜亮,只好再添。
就这么翻来覆去试了十多次,朱杏终于在染料的用量和最终色彩间取得微妙平衡,但有个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料子发硬。
这个问题染布前她们就想到过,可等成品真的拿在手中却发现无法接受。
七娘急得挠头,“染料的分量已不足霞染的三成,够少了,怎么还这样呢?”
发硬,不够柔软,就飘得不好看!
朱杏边洗手边说:“胚布太过轻软,没有筋力,拗不过。”
况且她们做的不是单色染,而是多种染料叠加的叠色染,有的染料是源自植物的水样液体、膏体,遇水即化;有的却源于矿石,本身就重,叠加之后,更是雪上加霜。
之前的霞染是春秋穿的中等厚薄的缎子,差不多有四层轻纱那么厚实,本身颇具分量、垂感,有点染料也透不过背面、拉不过经纬,自然无关紧要。
可眼前的轻纱过分轻薄,染料水一沾就透,凝固后的分量甚至比丝线本身更重,便如裹了一层蜡的烛心,自然硬挺。
明月也过去搓了把脸,“很好,问题清晰,关键是怎么解决呢?”
身上也粘腻腻的,洗完手,顺便用手巾把脖颈、前胸和后背都擦一遍,微风拂过,可得片刻清爽。
端午节之后,染坊上空就撑起大匹大匹的麻布,在地上投下大片阴影,热力骤减。下小雨不用管,若下大雨时,只需拉动两侧绳索,上方的遮阳布便会船帆般向两侧隆起,非常方便。
只是天气越来越闷热,稍一动弹就一身汗,明月便不许男人进后院,她们几个都只穿一件裹胸,既凉快又方便干活。
七娘也过来洗脸,她甚至突发奇想,“不然咱们先染了丝,再叫徐掌柜那边按着稿子用染色丝线织布?”
明月沉默片刻,平静道:“你说的那个法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缂丝。”
七娘:“……”
真要在胚布上做花色,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刺绣、提花、缂丝等等,可为甚么不做呢?
成本高呀!
不会呀!
朱杏跟着扯扯嘴角,突然想起什么来,转身进屋。
明月和七娘对视一眼,也跟着进去,“怎么了?”
朱杏抱出一罐染料,抓了一点在指尖捻动,“我在想,这些染料对细纱而言是否太过粗重?若再细一点、轻一点,浸透丝线后也许就能随水流走,便不会这样硬挺了。”
说干就干,明月当即派人去买来市面上最精巧的碾子、石臼,召集人来将几样染料反复碾过,果然肉眼可见的细了许多。
明月的手皮肉最细,伸手去摸时,只觉柔如棉、细若丝,不禁信心大增,再次染过。
还是硬!
确实软了一点,但比预期中的云雾烟霞般的柔软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