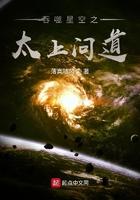秋天小说>让你当县丞,你把国运刷满了? > 第68章 长公主的信我的宣战书(第1页)
第68章 长公主的信我的宣战书(第1页)
淮安府衙的大堂,快要被吵翻了天。
重建,远比战争更考验人心。
血腥气尚未从砖石的缝隙里散尽,新的欲望与仇恨,便己在废墟上疯狂滋长。
“陈侯爷!王家的地契上百年了,凭什么划给张三那个短命鬼?他爹可是被我爹打断过腿的!”一个穿着绸衫的乡绅唾沫横飞,指着人群里的一个汉子。
“放你娘的屁!我爹那是上你家讨债被打的!”汉子双眼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
“侯爷!我们家男人死在城墙上了,分的地竟然跟赵屠户家一样!他赵屠户守城的时候,可就躲在家里磨刀!”一个妇人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喧嚣,哭喊,咒骂,混杂在一起,让整个大堂嗡嗡作响。
三天前,封侯的圣旨抵达淮安,整个府城都沸腾了。
他们的陈县丞,一步登天,成了大厦王朝最年轻的侯爷。
百姓们与有荣焉,走在路上腰杆都挺首了几分。
可荣耀的光环下,是“分田”这块被投进欲望深潭的巨石,激起了所有人的贪念与妄想。
陈默端坐于公案之后,手指无声地敲击着桌面,冷漠地注视着堂下上演的众生相。
贪婪,愤怒,期盼,嫉妒……
他曾用这两个字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现在,这火焰开始灼烧他自己。
“肃静!”
石敢当怒目圆睁,手中惊堂木重重砸下,那炸雷般的声响,总算让鼎沸的人声稍稍停歇。
陈默抬了抬手,示意他退下。
他站起身,缓步走下公堂。
皮靴踩在冰冷的地砖上,发出清脆而富有节奏的声响,每一步,都像踩在人们的心跳上。
他停在那个绸衫乡绅面前。
“你说,不公?”
乡绅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却还是仗着宗族势大,硬着头皮道:“当然不公!我李家在淮安盘踞数代,他张三算个……”
“守城之战。”陈默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压过了所有杂音,“你李家,捐了几石粮,出了几个人?”
乡绅的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陈默没再看他,目光转向那个为丈夫哭嚎的妇人。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妇人哽咽着回答:“回侯爷,叫……叫王铁柱。”
“王铁柱。”陈默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他是英雄。”
他转过身,面向堂内外的所有人,声音陡然变得森然。
“我陈默分田,不看你家祖上阔没阔过,不看你跟谁是亲戚,更不看谁的嗓门大,谁的眼泪多!”
“我只看一样东西!”
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府衙外那片正在施工的空地。
“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