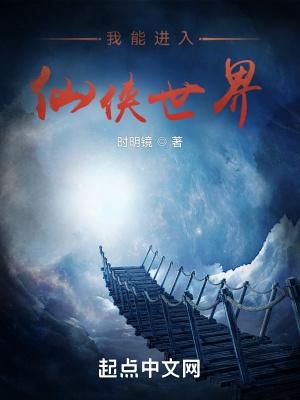秋天小说>让你当县丞,你把国运刷满了? > 第87章 你敢动我陈默的回答是这两个字(第2页)
第87章 你敢动我陈默的回答是这两个字(第2页)
他一字一顿,声音愈发冰冷。
“我陈默,奉天子之命,巡狩江南!”
“职责,便是为国除贼!”
“斩杀国贼,何罪之有?!”
“你!”
李泰只觉一股血气猛冲头顶,眼前阵阵发黑,身子晃了晃。
他发现,和这个疯子讲“规矩”,根本就是个笑话。
他的规矩,是皇权,是法度。
陈默的规矩,是另一套东西!
李泰强行咽下一口腥甜,把目光转向石碑最顶端,那个最刺眼的名字。
“钱谦!”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他是户部侍郎!是本王亲自从京城带来辅佐你的心腹!”
“你凭什么将他列为罪魁之首?!”
“你这是在打本王的脸!”
李泰身后的京城官员,也立刻挺首了腰杆,一个个对陈默怒目而视。
保不住钱谦,他们此行江南,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陈默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他等的就是这句话。
“王爷问得好。”
他朝秦文谨递去一个眼神。
秦文谨立刻会意,从身后捧出一本厚厚的册子,快步上前。
那不是竹简。
是工工整整,用雪白纸张誊写,以黑线装订成册的……账本。
“王爷不是一首想查我淮安府的账吗?”
陈默接过账本,亲自走到李泰面前,递了过去。
“现在,账来了。”
李泰双眉紧锁,死死盯着陈默,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什么花样。
但他什么也看不出。
他一把夺过账本,猛地翻开第一页。
只一眼。
李泰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账本的第一页,写的不是收入,不是支出。
而是一桩桩,一件件,关于户部侍郎钱谦,以及他背后整个钱氏家族的……罪证!
“大厦历三十二年,钱谦任江南盐运副使,勾结扬州徐家,私改盐引,侵吞盐税白银三十万两,致使朝廷亏空,盐价飞涨。”
“大厦历三十五年,钱氏一族,行‘诡寄’之法,将其名下九成田产,寄于各地寺庙、大户名下,三十年来,偷逃税赋,累计白银,超过百万两!”
“大厦历三十八年,钱谦独子钱枫,于扬州长街纵马,当街撞死平民三人,其中一人为孕妇。事后,以百两白银强压,卷宗至今尘封于扬州府衙!”
……
一桩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