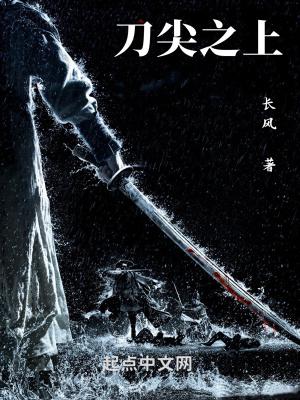秋天小说>恶圈 > 壹拾(第3页)
壹拾(第3页)
车后面有片杨树林,他们站在树下。风一来,涌来春意勃勃的花草气息。远处林子里,不时传来一阵悠长急促地婴儿哭似的猫叫春声。
梦秋双手背在身后靠在杨树上,笑吟吟看着修浔,脸颊微微泛红。
“你现在就还。”梦秋偏过头去,脸颊更红了。
“我……我……没带钱。”修浔窘得脸通红。
“哎呀……真笨!”梦秋脸贴在修浔的胸脯上,双手紧抱着修浔。梦秋听到修浔心脏在胸膛里猛烈地鼓动,搏击着她贴在他心上的半边脸上。
修浔慌忙边推她,边四处瞅视,心都快蹦出来了。天热得让人窒息,四周无人,只有远处急促地猫叫春声。梦秋抱得更紧了。
“不不不不!”修浔用力推开她。
“你欺负我,”梦秋说。“哼!我告诉仁杰去。”
“你胡说啥!?”修浔脸色又红又白,声音又尖又颤。
“哎呀!”梦秋连忙笑道。“你当真了?”凑到修浔跟前仰着脸看着他,又抱着他,比上次更紧了。
修浔又慌忙四处瞅视,心突突狂跳,双腿不住地颤抖。她抱得很紧,推不开,也不敢太用力。他额头、手心出满了汗,浑身僵硬。
梦秋松开了手,头靠在他肩上,仰起脸低声说:“吻我。”说着害羞得闭上了眼,微低了头,脸颊微红。杨树间隙泻下金黄的阳光。梦秋的脸,泛着金光,乌发映在阳光里,金光闪闪。梦秋似乎发觉了他在看她,睁开了眼睛。
修浔低头不敢看她,可是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都是她。
“吻我。”她轻声喃语。没有闭眼睛,反而睁大眼睛。眼里透出两道明媚的亮光。修浔大口喘气,连忙偏过头去,转身离去的念头在脑中打转,脚却挪不动。梦秋扬起胳膊勾住修浔的脖子,一股奇异的气息涌进修浔的鼻腔里,他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喉结半天才抖落下来。浑身酥麻,渐渐溶化。
修浔心里一股奇异的劲头想把她的身体溶进自己的身体里。他紧紧抱住她,找到她的嘴唇贪婪地咬着、吮着。梦秋半闭着眼睛,身体软软的往下掉。梦秋的舌头顶着修浔的牙,似乎要他张开嘴。那一瞬,他突然明白了,张开了嘴,急切的伸出舌头与她的舌头交融在一起。那一瞬,他全身鼓胀。梦秋温热软软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肋骨已被熔断。那一瞬,他突然觉得压在心里的石头少了,仁杰终于不会再对他好了,整个人轻了,像漂浮的羽毛。
修浔忘情地吸吮着,梦秋引导着把他的手放在她的**上。他几乎昏晕了,无师自通地轻柔着那个软弱无比美好无比的**,再也无法抑制内心涌出的洪流。一股强电在涌动,快要喷发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仁杰,他再也不会爱自己了,他突然感到无比的恐惧,全身发抖、牙齿打颤,他更加猛烈地吸吮着她的舌头,用力的抓揉着她的**。那股强电终于喷泻而出,他紧紧地抱住她,想在她怀里死去,想叫她妈妈。
他久久地紧紧地抱着她,风轻拂着身旁的杨树、地上的花草,杨树下闪着斑斑驳驳的金黄的光。他嗅着她的脖颈、她的脸、她的头发,他拼命地吸着她身上的气息。他想让她所有气息流淌在他身体里。如果妈妈在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气息?已经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了,他眼泪流了下来,他抱得更紧了。
“走吧。”他说,悄悄抹去泪。
“就不让你走。”梦秋笑道,咬了咬他厚厚的下嘴唇,仰起脸望着他笑。
红色的轿车奔驰在公路上,两旁树木疯狂地倒着带,可他不能了。太阳又上了些,天更热了,所有东西变了形,冒着S型的热气。墨镜遮住了梦秋半边脸,那张红唇显得格外艳丽,一张一合带动着雪白鲜红的笑脸。修浔在后视镜里检视着自己。他看到后视镜里的那个人惶惶不安、后悔、无助、不知所措纠缠在一起。湿粘的**贴在大腿上,很不舒服。他没有动,浑身酸软,似乎没有一丝力气。想到刚才的一幕,他冷汗直冒,浑身发颤。
“你们……”梦秋笑着说。“真的分开睡的?”语气中透露着怀疑。
修浔瘫靠在副驾驶座位上,呆呆地盯着前方。
好一会儿,他才微微点了点头。
“为什么?”她问。
修浔皱起眉头。
回来后,修浔没敢跟文秀和仁杰有过任何眼神交流。梦秋依然与文秀说说笑笑,似乎根本没发生过什么。
他进房换衣服时没反锁房门,好像一反锁文秀和仁杰就会怀疑到什么。他匆匆脱掉外裤,慌忙穿上新买的裤子。黏糊糊的**没敢换,他怕他一换,文秀冲进来发现。文秀从来没在他换衣服时进来过,但此刻,他觉得她就会进来。再说脱下来放哪?放哪不会被发现?他想不出来,脑子一团浆糊。仿佛那已不是**,而是一颗摁了倒计时的炸弹。换完衣服他发现自己全身湿黏出满了汗。
文秀坐在修浔左边,梦秋坐在修浔右边。梦秋不时给修浔夹菜,够不着就站起来旁若无人给他夹。
“这个好吃,你尝尝。”她说。
修浔很感激,但觉太过惹眼,又不敢说什么。一点胃口都没有,象征性地吃上一两口。别人找他碰酒,喝完酒坐下时顺势看了一眼文秀和仁杰的脸,分析着他们的表情是不是看出些什么。
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抽烟的手控制不住地一直在发抖。他从来没有连续抽过两根。现在他已经连续抽了六根了,抽第七根的时候,旁边的朋友笑道:“你看这瓜怂,今天干啥亏心事了,抽烟抽个反反都不知道。”原来他把烟抽反了,烟吧都快抽完了也没发觉。
他以为仁杰和文秀听到这话,就会发觉他们的事。顿时头晕目眩,浑身发软,觉得自己马上要从凳子上跌下去了。
“别抽了,”梦秋说,“今天你都没怎么吃,不是抽烟就是喝酒,胃能受得了?”说着给他舀了一碗酸辣肚丝汤,放在他跟前。他顿时鼻子发酸又看了仁杰一眼,仁杰的脸憋得红胀,才想起来他是闻不惯烟味的,多年来在他跟前已没抽过烟了,连忙灭了烟,也让同桌的几个人灭了。
仁杰开车把他们送到楼下,梦秋喝多了,斜在副驾驶上睡了。
“她怎么那么骚情?”一进门文秀就对修浔说。“穿得那么妖不知道给谁看呢?人家来跟你碰杯,我还没说啥呢,她凭什么挡?她凭什么替你喝?真是,鸠占鹊巢!不知道自己是谁!”文秀脸胀地通红,重重地喘着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