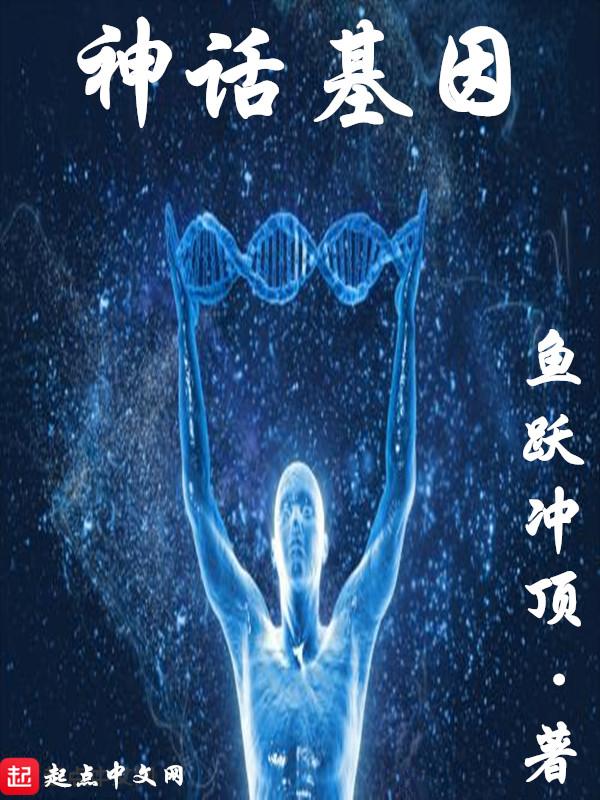秋天小说>被迫逃荒后,我靠位面系统养活全家 > 第一百零四章(第1页)
第一百零四章(第1页)
谭瑛晚上起夜去上厕所。
她裹了裹衣裳,瑟缩着肩膀要往回赶,肚子还是胀胀的难受,鼓起了一个圆滚的弧度,衣裳里面绑着个手炉。
是余敬廷给买的,一个小猪造型的铜手炉。
里面放了块热热的火炭,隔着炉套子焐在小腹很暖和。
倏地。
正房的门被吹开了一个缝儿,那门缝越吹越大,发出幽森如鬼的吱呀声,她视线看过去,只听见屋里传来不大不小的响动。
女人瘦削如鬼的身影突然从里面晃出来,很艰难的样子,吓了谭瑛一跳,发出抽吸的惊呼声,心脏怦怦直跳。
“你。”
“你没事吧?”
女人似乎才注意到院里站着的谭瑛,月光打下惨淡的一层白光,月余未见,她似乎更有精神气了,明亮的眼,柔韧的腰身,整个人都充斥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看了就叫人嫉妒。
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原本打仗参军的丈夫回来了,还当了个小官。
她没说话,头昏脑胀,强忍着下身靡烂灼烧的疼痛,想要将大开的门关上,脚下迈过门槛的时候却被绊了一下,整个人头朝下摔了下去,沉闷的钝响夹杂着隐隐的闷哼声。
谭瑛犹豫了下,还是过去了。
她把女人给搀扶起来。
扑鼻一股腥臭的味道,熏得谭瑛差点没吐出来,她憋住气,调整好情绪,将人给安稳妥帖地扶进了屋子。
“水在哪里,要不要我给你倒些水?”
没有回音。
谭瑛索性借着月光四下打量了一番,比她家住的那间房大多了,虽宽敞却不显得空荡。
梳妆台,八仙桌,拔布床……家具很全,不过都是极旧的成色,像是从不知哪儿淘来的几手货。
床边立着个高而窄的铜烛台,蜡烛燃了一半,谭瑛先去重新把火烛点上,然后把打开的门关好。
屋里亮着暖黄色的光,谭瑛给她倒了半碗水,没办法,壶里只剩下这么点儿水了,底部还铺有一层厚厚的水垢。
女人半倚着坐起来,脸色惨白,皮肉可怕的水肿起来,眼泡痕迹很重,动作迟缓僵硬地接过了递来的水碗。
看样子那处的炎症把她折磨的不成人样。
谭瑛看着她呆滞喝水的动作,突然问系统。
“她会死吗?”
K沉默了一会儿,言简意赅道,“不吃药的话,活不过一个月。”
听见回答,谭瑛微不可察的皱了下眉。
“你怎么不用药?”
观这屋里陈设,女人绝非穷困潦倒之辈,那为什么不买些药吃,反而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