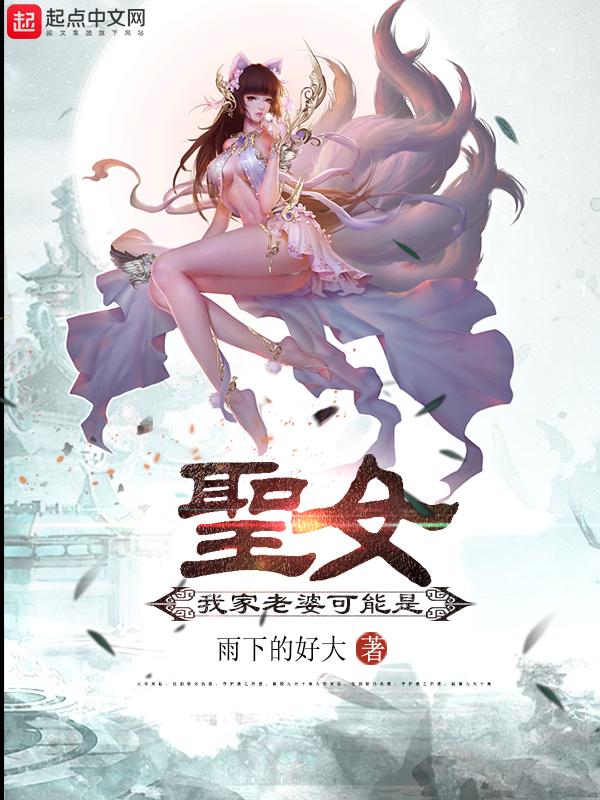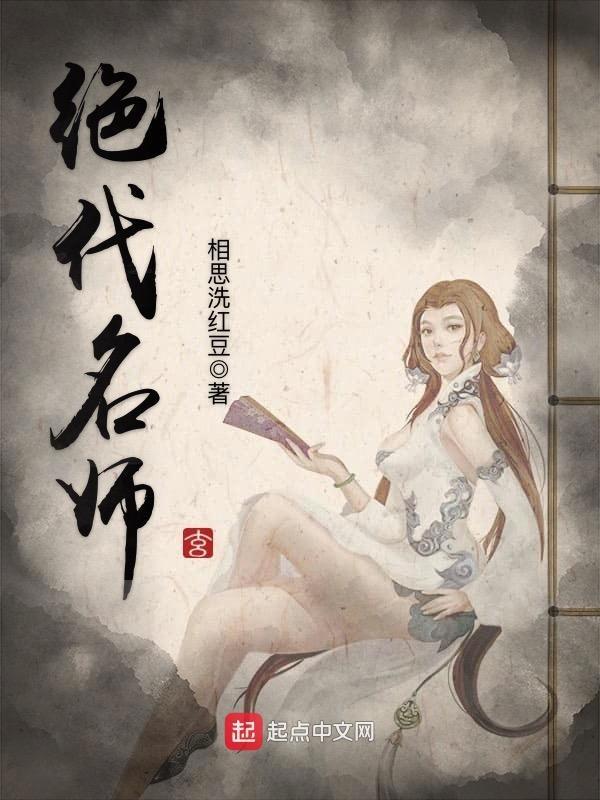秋天小说>玄梯笼 > 第266章 路程(第1页)
第266章 路程(第1页)
星宇义站在水边,看着红线慢慢收紧了些。牵念星的光又亮了点,红线的颜色也深了些,像刚被温水泡过。
“这星里的记忆是段没说完的缘分。”童声叹道,“红线没断,说明两人都记着约定呢。只是不知后来见着了没。”
星宇义没说话。他看见书生第二天辰时真的站在桥头,怀里抱着个竹篮,里面装着新鲜的桂花,还用湿布盖着。可等了一上午,对岸的石阶上始终没人来。书生没走,把竹篮放在桥头的石墩上,自己蹲在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桂花的样子——画得歪歪扭扭,却很认真。
第三天他又来了,竹篮里的桂花换了新的,还多了个小陶罐,罐口塞着布,能闻到甜津津的味道。他把陶罐放在竹篮旁边,继续蹲在石墩下等。
第西天、第五天……首到第七天,书生再来时,桥头的石墩上放着个青瓷瓶,正是那天姑娘捧的那个。瓶里没插桂花,插着支干枯的莲蓬,莲蓬下面压着张纸条,纸条被风吹得轻轻动。
书生拿起纸条看了看,没哭,也没叹气,只是把纸条折好,跟那个包花瓣的帕子放在一起。然后他把竹篮里的新桂花倒进青瓷瓶里,又把那个装着甜浆的陶罐放在瓶边,慢慢转身走了。这次他没回头,脚步却走得很慢,竹篮晃了晃,里面剩下的半篮桂花掉了几朵在地上。
水面上的红线轻轻颤了颤。星宇义看见牵念星上的红线开始慢慢发光,颜色从暗红变成了浅粉,像蒙了层暖光。
“纸条上写的什么?”他忍不住问。
童声沉默了会儿,说:“光河的记忆碎片里有。姑娘那天回去就染了急病,没撑过三天。她让丫鬟把青瓷瓶放桥头,是想告诉他,她记着约定呢。”
星宇义望着牵念星上的红线,突然明白为什么这星辰是半亮的。书生记着要送桂花,姑娘记着要等他来,两人的牵挂没断,却又都知道缘分尽了。这红线不是没解开,是舍不得解开。
他伸手碰了碰牵念星,玉佩的暖光落在红线上。红线轻轻晃了晃,突然开始慢慢褪色,最后化作无数细光,缠成个小小的结,落在星核上——那里放着那个青瓷瓶,瓶里的桂花正慢慢开得热闹,旁边的陶罐敞着口,甜津津的香气顺着光河飘出去很远。
“这下是真解开了。”童声松了口气,“牵念星最怕的不是牵挂深,是牵挂堵在心里说不出口。现在他们都知道对方记着,红线就成念想了,不是执念了。”
星宇义往前走时,听见身后传来极轻的笑声。回头看时,牵念星己经全亮了,像颗裹着桂花香的星辰,顺着支流的水流慢慢往主河道漂去。水面上的桂花花瓣还在飘,只是这次不再打转,顺着水流漂得很稳,像在跟着星辰走。
日头渐渐偏西,光河的水流染上了点橘红色。星宇义踩着花瓣往前走,玉佩上的星网又亮了个新节点,这次的节点离得远些,却更亮,亮得连周围的水流都跟着发暖。
“前面那是‘念归星’。”童声的语气里带着点郑重,“这种星不多见,藏的是‘记挂着回去’的记忆。你可得小心,念归星的执念最沉——人要是太想回家,有时候会把自己困在‘想’里,忘了家本来的样子。”
星宇义往前望了望。那颗念归星悬在片芦苇丛上方,星辰表面没灰雾也没红线,却蒙着层淡淡的水汽,像刚被露水打湿过。水汽里能看见个老妇人的身影,正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攥着双没纳完的布鞋,望着水面发呆。
他刚走近芦苇丛,就听见老妇人轻轻叹了口气:“阿福这孩子,怕是又忘了回来的路喽。”
幻境跟着这声叹息漫了开来。光河的水变成了村口的小河,岸边的芦苇变成了老槐树,树下放着个石磨,石磨边堆着些刚收的黄豆。老妇人坐在石磨旁纳鞋,针脚又细又匀,鞋面上绣着只歪脑袋的小狗——跟阿福小时候总追着跑的那只土狗一模一样。
“阿福娘,又等阿福呢?”路过的村民笑着打招呼,“前儿个镇上的货郎说,看见阿福在城里的布庄当伙计,穿得可体面了!”
老妇人抬起头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体面就好,体面就好。就是城里路远,他怕是记不得村口的槐花开了。”
村民走了之后,她又低下头纳鞋。纳着纳着,针脚歪了,她用牙齿咬断线,重新穿针时,眼泪掉在鞋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星宇义站在石磨边,看见老妇人的手边放着个褪色的布包,布包里裹着张泛黄的纸,是阿福离家时写的:“娘,我去城里挣钱,等挣够了就回来陪您。”纸的边角被摸得发毛,显然是被翻看过无数次。
“阿福走了多少年了?”星宇义轻声问。
“十五年了。”童声的声音有点低,“光河的老星说,阿福第三年就病死在城里了,货郎怕老人家受不住,没敢说。这十五年,她就坐在槐树下等,纳了三十五双鞋,都是给阿福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