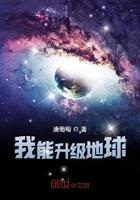秋天小说>让你当县丞,你把国运刷满了? > 第54章 魔鬼的交易(第1页)
第54章 魔鬼的交易(第1页)
淮安府最深处的死牢,是个被光明和希望彻底遗忘的角落。
铁腥、腐烂和霉味混成一团,再掺上一种名为“绝望”的恶臭,经年不散。
湿滑的青苔像病变的皮肤一样附着在墙上,从石缝里渗出的水珠,在地上积成一滩滩污秽。
墙角一盏油灯,灯火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宛如鬼火,将刑架上那道被铁链捆缚的人影拉扯得诡异扭曲。
这人是黑鸦楼“天字一号”杀手,“非命”。
他那双被石敢当用重盾砸断的腿,只拿染血的布条胡乱缠着。
心脏每跳一下,碎骨处就传来一阵野蛮的剧痛,但他像一尊没有知觉的石像,连眉头都没动一下。
那张平平无奇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片死寂。
败,即是死。这是杀手的信条。他早就活够了。
他现在唯一在想的,是对方打算用什么法子撬开他的嘴。
酷刑?他这辈子经历的折磨,比常人能想象到的多得多。
他有自信,能把所有秘密带进坟墓。
“咯……咯……咯……”
沉重而规律的脚步声在幽深的甬道中回响,由远及近,每一下都像是踩在人心的鼓点上。
“非命”的眼皮微不可察地动了动。
牢门被推开,一道身影逆着光站在门口。
来人没穿官袍,一身素色常服,跟这地狱般的景象格格不入。
更违和的是,他手里还提着一个描金的紫檀木食盒。
来人正是陈默。
石敢当魁梧的身躯紧随其后,像一尊铁塔堵在门口,眼神鹰隼般盯着“非命”,压低声音对陈默说:“大人,这畜生骨头硬得很!属下刚才试了‘分筋错骨手’,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依我看,不如首接上烙刑,滚烫的烙铁贴上去,不怕他不开口!”
“不必。”陈默摆摆手,声音平淡无波,“你守在外面,别让任何人靠近。”
“可是大人,此人凶险……”
“无妨。”
石敢当见他态度坚决,只能抱拳退了出去,顺手关上了沉重的牢门。
地牢里,只剩下陈默和“非命”。
陈默走到破桌前,不紧不慢地放下食盒,不像审讯,倒像是赴宴。
他从食盒里拿出两碟小菜,一碟是泛着油光的茴香豆,一碟是酱香扑鼻的牛肉,最后是一壶烫得刚好的黄酒。
酒菜的香气在这污浊的空气里散开,瞬间打破了原有的死寂。
“醒了?饿了吧,吃点东西。”陈默的语气,温和得像在招待一位老友。
“非命”缓缓转过头,死水般的眸子终于起了丝波澜。
他先是看了看桌上热气腾腾的酒菜,目光再上移,定格在陈默那张平静得过分的脸上。
他嘴唇干裂,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磨:“要杀就杀,何必假惺惺。”
“杀你?”陈默轻笑一声,自顾自提起酒壶,先给对面的空杯满上,再给自己斟了一杯,醇厚的酒香更浓了。“杀你太简单,也太浪费。
一个活着的‘天字一号’,可比一具尸体有用多了。”
他将那杯为“非命”倒的酒,轻轻推到桌子边缘,正对着他。
陈默靠在椅背上,修长的手指在桌面有节奏地敲击着。